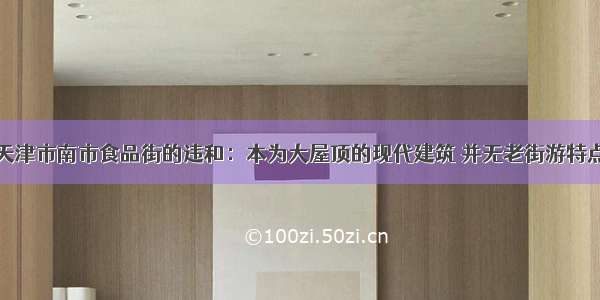编者按:此文是作者学位论文研究过程中的副产品。大屋顶那么多人在做,他们背后的观念是什么呢,有何差异?本文只是一个粗略的梳理,所选案例有限,挂一漏万,算是抛出一个砖头。原文为《中国建筑教育》清润杯论文竞赛硕博组的获奖论文,标题为《大屋顶变形中的历史意识与设计探索——从象征到表现》,在此略有更改。
中国历史中的木构建筑,就其外观来说,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出檐深远的大坡屋顶。在论及中国建筑的特征时,梁思成写到“屋顶不但是几千年来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并且是我们民族所最骄傲的成就。它的发展成为中国建筑中最主要的特征之一”[1]。过去百余年来,大屋顶不仅是过去的历史,还不断深刻地影响到现实中建筑学实践。从来没有什么能比大屋顶更能满足人们对于民族形式的想象,虽然对于它的批评从未断绝。
师法古人和经典是文艺创作常有的现象,其微妙之处在于选择模范的对象与方式。关于这一点,历来被尊为“诗圣”的杜甫也有过议论:“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诗经》历来是所有诗人共同学习的经典,不过,在《诗经》的诸多篇章中,杜甫特别提到了应该学习其中的“风”和“雅”;“亲风雅”而不提“颂”,体现了他对于历史范例选择中的价值判断。
本文将选取几个代表性的案例,考察分析过去一段历史时期对坡屋顶的不同建筑处理,目的是辨析建筑师在选择历史案例和处理手段上的差异,以及价值观念上的变化。大屋顶通常都是指官式建筑的屋顶,不过,本文试图讨论中的屋顶不独指官式建筑的屋顶,也包括传统民居中的坡屋顶。这两类坡屋顶如果只是形式上或结构的差异,显然不足以特别做区别。在将中国历史建筑风格特征和西方古典建筑构图原理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的大屋顶和西方的穹顶是可以类比,具有相似的象征价值。古典空间观念,大屋顶下是一个完整的空间单元,具有象征性意义,它的纪念性、象征性远远大于功能性,其单一的大屋顶/穹顶的形式与功能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一致的。官式大屋顶和普通的民居坡屋顶有着象征价值上的差异,官式大屋顶一般是位于象征性空间之上的,具有强烈的礼仪特征和价值的象征意义;而民居的坡屋顶主要是功能性的,象征性意义比较弱。一个具有纪念性,另一个不具有纪念性。这似乎使他们产生了古典意义上的价值差异,一个是大写的建筑,而另一个只是房子而已。因此,当建筑师在选择不同的历史案例和师法对象时,就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判断和选择。
梁思成:作为价值象征的屋顶
1935年,梁思成为兴业建筑事务所徐敬直设计的南京博物院参谋,以准确地再现辽代风格[2]。之所以不是唐代风格,因为此时他还未发现佛光寺大殿。此前民族固有形式的探索已经层出不穷,例如吕彦直设计的中山纪念堂和中山陵,董大酉的上海市政府新屋(1934)等等。但是在梁思成看来这些先例都不够经典,因为他们的模范是明清时期的建筑式样;这在他看来是羁直僵化的风格代表,属于衰落时期的艺术。所以在南京中央博物院的设计中,梁思成极力促成了一种辽代风格的再现,正如赖德霖的研究让我们看到的那样,无论是建筑结构和装饰构件都比较精确地模仿了辽代建筑实例(图1,图2)。然而除了材料的替换之外,它相比那些先例并没有更多的改进。相反,董大酉的上海市政府新屋会议厅上巨大的混凝土桁架屋顶看起来更具有一种技术上的成就,它提供了一个无柱的空间以满足下面大会议室的要求(图3)。
图1,南京博物院,1948年主体结构完成,裸露的混凝土屋面。琉璃瓦屋面由刘敦桢1952年设计完成
图2,南京博物院,斗拱、檐口用混凝土浇筑密集的装饰性飞檐椽
图3,董大酉,上海市政府新屋剖面,屋顶为混凝土桁架
南京中央博物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尝试,它必须满足更多的功能需要,实际上是一个多层的建筑。但是处于形式上的考虑还必须把它统一在一个大屋顶下,看上去象一个单层的建筑。而且钢筋混凝土的结构尺度(跨度和构件比例)也要和木结构一致,实际上无法发挥新材料的优势。南京中央博物院是折中主义典型,他固守一种先验的美学原则和价值观念,而不顾功能的实际,与现代建筑的价值完全背道而驰。然而,建筑史学者赖德霖却认为:梁思成参与的南京中央博物馆堪称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纪念碑,它是中国的,同时又是世界的和现代的[3]。这一结论充满了矛盾之处,他努力详尽的分析似乎最终只是为了显而易见的折中主义辩护。现代建筑在赖德霖看来完全是中性的名词,而不具有一种意识形态涵义。梁思成将他的中国建筑史学的研究运用到博物馆的设计中,使之更符合辽代的风格特征,并使这种风格在结构上更为合理,但无法改变的是建筑观念中复古和折中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精确的忠实的仿古建筑”。
1964年,梁思成设计了扬州鉴真纪念堂,这个面阔五间、进深三间的小纪念堂直到他去世后两年之后才建成。纪念堂借鉴了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的布局和形式特征,采用唐代佛殿的建筑风格。此事对梁思成来说意义重大,因为他终于可以亲手设计一座唐代风格的宫殿,回应了在他在1937年发现的五台山佛光寺。
佛光寺大殿的重大发现使梁思成于1942年写成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一本面向西方读者的简明扼要的中国建筑通史。这本书直到1984年才在美国出版,副标题是“关于中国建筑结构体系的发展和类型进化的研究”[4]。他将中国北方官式木构建筑遗物称为纪念性的(monumental)建筑,并将它们分为豪劲、醇和、羁直三个时期。这三个词语带有明显的美学判断,梁思成实际上建立了一个价值系统,其最高价值体现在唐代的建筑风格中——豪劲。但是这种历史叙事还暗示了一种生命体的衰落,只是死亡并未言明。假如在历史主义“发展”和“进化”的观念下,西方建筑史是多种风格的不断更替,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只描绘了一种风格的兴衰。然而,衰落之后是什么呢?梁思成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中说道:“无疑的将来中国将大量采用西洋现代建筑材料与技术,如何发扬光大我民族建筑技艺之特点,在以往都是无名匠师不自觉的贡献,今后却要成近代建筑师的责任了。如何接受新科学的材料方法而仍能表现中国特有的作风及意义,老树上发出新枝,则真是问题了”[5]。在西方现代建筑新潮的冲击之下,这是梁思成最为关心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直以来困扰中国建筑界的“梁思成问题”。这个问题或许并非梁思成首次提出,但是梁思成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具有代表意义。新技术对历史建筑的风格和技术全面冲击而不可避免,虽然在理智上梁思成已经认识到历史传统的局限,但情感上却不舍传统的价值,时时想“梦回唐朝”。
戴念慈:屋顶的旧形式与新内容
梁思成是公认的中国建筑史学的开山鼻祖,在某种程度上,他所代表的学派属于中国建筑界主流,在学术和实践方面影响了后来的几代建筑师,戴念慈就是其中的一位。戴念慈并非直接在梁思成门下就学,而是杨廷宝的学生。他曾在兴业建筑师事务所工作,负责南京中央博物院建设后期的工作,并看到梁思成的设计手稿,对他的理想与局限也有实际的了解 [6]。然而戴念慈并非是梁思成思想的信徒,他早期受赖特的影响,强调形式和内容的一致性、真实性,对民族形式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而且其态度不可谓不激烈,“宫殿式的北京图书馆和宫殿式的金陵大学,都是谎。它们都是钢骨水泥的构造,然而都装扮成一副木构建筑的面貌”[7]。无疑这种批评对南京中央博物院同样适用。此时戴念慈坚信,新的内容必然带来新的形式。然而这种思想并非始终如一,到了晚年,他并不排斥民族形式或旧形式的采用,他认为将旧形式依据新的内容进行改造,就是推陈出新 [8]。
阙里宾舍(1982)是80年代的最著名的建筑工程之一,这一建筑基地紧邻历史悠久的曲阜孔庙。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采用一种历史形式并不奇怪。宾舍的中央大厅屋顶是这座建筑的皇冠——十字脊歇山式屋顶(图4)。这个屋顶实际上是一个正方形的伞型薄壳结构(边长约12米),支撑点在正方形大厅的四角。山墙开满玻璃窗,自然光从四面进入内部空间。覆盖在中央门厅空间的大屋顶,结合了天光,概念非常接近西方建筑中的穹顶,笼罩在穹顶下是一个较单一的、完整的空间(图5)。但是,穹顶光洁平滑的内部空间和外部的传统屋檐装饰形成明显的反差,外部装饰得像歇山顶,檐口用混凝土浇筑密集的檩条,仍然是对木结构的模仿(图6)。在结构技术上,戴念慈超越了他的前辈,同时他也抛弃了梁思成对传统梁架结构体系的表现的执著。这种扬弃是含蓄的,因为从外部看来,他很恰当地保留了历史建筑的形式特征,将伞壳结构屋顶的表现包裹在历史建筑形式的外衣里。
虽然使用当代的技术手段构造大屋顶,但是这个屋顶在其价值观念上仍然是作为传统的象征。在80年代民族形式的论战中,戴念慈也是讨论的中心人物之一,但他并不赞同神似和形似的两分法,反而认为传统价值和其形式是不可分离的。戴念慈希望旧形式仍能和新的功能相结合,利用现代技术是为了使旧形式新内容重新具有一种合理的逻辑关系,从而使旧形式再次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在这一点上, 阙里宾舍是对“梁思成问题”的一种回答。
图4,阙里宾舍,大厅的四支点伞壳屋顶包装成传统十字脊歇山顶
图5,阙里宾舍,大厅内景,光滑的薄壳屋顶
图6,阙里宾舍,檐口用混凝土浇筑密集的装饰性檐椽
葛如亮:追随地形的屋顶
葛如亮50年代初曾在梁思成门下做研究生,毕业后回到上海同济大学任教。不过,他在80年代的实践中并没有表现出受其导师过多的影响,这或许是因为在上海浸染了现代建筑思想的缘故。而实际上,梁思成的思想也并非僵化不变,他对于地方建筑风格差异是敏感的,认为在南方仿古建筑应该轻盈、灵巧,不宜如北方官式建筑“堂哉皇哉摆架子”[9]。葛如亮选择的历史案例和师法对象已经转移,转移到民居或者乡土建筑中。他对其故乡浙江山地的乡土建筑怀有深厚的感情,对地方民居、寺庙有过比较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建筑与自然的关系、山地民居和地形的结合——“天台山区民居与环境结合得非常自然协调,浓厚的乡土气息是由当地材料、生活习惯和地区气候条件所赋予。在似乎漫不经心之中,显出它灵活多姿、不受囿束的特点”[10]。乡土建筑造型结合自然、活泼生动的特色,正是葛如亮所追求的价值。
习习山庄(1981)那段梯形的大屋顶顺应了地形的坡度,沿着地形的变化而生长。葛如亮的目的并不是企图从传统民居中寻找一种普遍性的特征,而恰恰是那些反常规的做法,这种反常规的形式并非武断的,而是建立在与地形、功能相契合的基础之上。葛如亮的原创性表现在这里,他没有采用传统的一系列逐层升起小屋顶的做法,而是将不同标高的踏步平台置于一个完整的坡屋顶下。在习习山庄,“形式追随地形”,屋顶形式表达了场地的个性,屋顶的坡度和地形一致,均为5.5:1。葛如亮在谈到这个屋顶时说,“灵栖习习山庄22.8米长坡屋顶,突兀坚强,引起了纷纷议论。无论是它的出现和对它的坚持,脱离不了我们对浙江山区地方性内在的理解和感受”[11]。习习山庄是葛如亮的呕心之作,是真正属于某个独特基地的建筑,施工图纸在现场经过了多次的调整,由于场地的地形复杂,在基础挖掘过程中,不断冒出地下的岩石。葛如亮保留了这些岩石,并将这些岩石参与到空间的营造中来(图7)。
葛如亮利用高低变化的、不稳定、非对称的屋顶引发形式的张力,并力图在结构形式和传统建筑形式的再现方面表现平衡。看起来,这片大屋顶的柱梁系统和密肋屋盖是分开浇注的,似乎有意模仿了传统的木屋架系统,而且这种模仿是建造方式上的模仿,不仅仅是构件形式的模仿。习习山庄的建造方式表述得非常清晰,尤其是混凝土屋盖的密肋次梁好像是预制的线型构件,直接搭接在水平主梁上,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构造效果(图8)。屋顶的做法体现了那个时代一种罕见的真实和清晰。
不同的两榀柱架之间通过水平的梁联系,好像在暗示木构中的“穿”。但是,在这个一泻而下的大屋盖下,尺寸粗大的水平穿梁似乎破坏了“流动空间”的完整性和视觉上的通透感;同时也导致穿梁与独立的片石墙产生了一种古怪的交接方式(图9)。此外,水平的穿梁在结构上是否必须也值得商榷,其结构作用是维持两榀柱架之间的稳定,假如柱基础足够强的话,穿梁就可以省略,而且即使结构上有需要,也并不一定非要做成水平的。因此不无疑问,这种有意对木构系统的再现仍然萦绕在建筑师的头脑中,彰显出梁思成思想遗产的余风犹存。
图7,习习山庄,顺应地形的坡屋顶
图8,习习山庄,柱、梁、密肋次梁和屋面板的搭接,清晰、真实、朴素。
图9,习习山庄,大坡屋顶下,尺寸粗大的水平“穿”梁似乎破坏了流动空间的完整性和视觉上的通透感
冯纪忠:“亲地”的屋顶
1978年,当冯纪忠在着手设计方塔园时,他一定面临着如何将传统建筑特征进行现代转换的问题,因为对于一个展现古代遗迹的公园,很难选择一种先锋的现代建筑形式而能得到甲方的接受。冯纪忠所面对的并非是一个新问题,他的维也纳前辈瓦格纳在19世纪末已经思考过这种问题,即如何使用现代工业材料来还原历史风格中的纪念性和象征性。北大门的类型接近寺院的山门,似乎也召唤着某种程度的纪念性。北大门在尺度上具有一定的份量,而形式却极为朴素。冯纪忠将双坡顶分解为两片各自独立的单坡屋面,一高一低,一纵一横。这种巧妙的分解和构成,使北大门看上去具有一种歇山顶的错觉。但是,屋顶的构造运用了工业厂房常见的轻钢桁架结构,由小截面的型钢构件组合而成(图10)。冯纪忠拒绝模仿传统木构中高等级的宏大梁架,而采用这种工业时代的轻型结构,与方塔园里的那些明清厅堂遗构形成明显的反差。正是将这种时代的差异鲜明地表达出来,才使得新旧相得益彰,此为冯纪忠所言的“与古为新”的应有之意。
在80年代众多坡屋顶形式的做法中,冯纪忠的方塔园北大门创造性地将坡屋面分解为两个单坡屋顶,这一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有重大的意义。通过对具有纪念性的坡屋顶的解构,从而使大屋顶的象征意义解体(在梁思成那里,中国大屋顶相当于欧洲古典建筑中的穹顶),形式与价值发生分离。这一轻微的动作解放了坡屋顶,使坡屋顶不再是某种象征意义的载体,而成为纯粹的建筑构件,或者抽象的空间界面。冯纪忠不是要回到历史建筑的美学中去,其目的不是为了再现历史形态和风貌,或者回归某种历史价值,分解重构的做法是完全现代的,具有一种批判性的态度。
对于冯纪忠来说,宫殿式建筑、民居和临时棚屋在“历史价值”上并无区别。几年后,冯纪忠完成了他最后一件作品——何陋轩,对于一个70岁的老人,这个棚屋或是对其一生的注解。竹屋顶在形式上暗示了歇山屋顶,但更来自于童年时对传统中红白喜事临时搭建的大棚的记忆。对竹棚的搭建,冯纪忠非常熟悉,在建国初期,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大学里的一些校舍和辅助建筑都由竹结构搭建。50年代的同济大学食堂,就是这种大型的竹棚屋,它同时还兼有大礼堂集会的功能(图11)。竹顶并不需要结构设计,竹匠的经验完全可以胜任。民间的竹结构能将材料的性能发挥到极致,而且通常不假装饰。本来希望竹节点全部采用绑扎,而不做榫卯,这既是民间的常见做法,也符合他对竹子的材料性能的理解,因为榫头加工可能会破化竹子的力学性能。但是施工单位似乎觉得绑扎过于简陋,刻意做出了榫卯节点。这损害了对结构受力特征的真实表达;冯纪忠觉得这种做法“显示出豪式屋架的幽灵难散”,暗示他对执着于传统结构形式表现的批评 [12]。
何陋轩屋顶的四向并不完全对称,有着微妙而精确的变化。南侧屋顶远远地伸向水面,和室内跌落的地坪是呼应的。东侧翼的屋顶也比西侧长,檐口更低。冯纪忠观察到传统大棚屋顶具有一种“亲地性”,由于屋顶的高度通常大于墙身或立柱的高度,显得屋顶如同匍匐在大地上,这种感受在官式建筑上就不大常见。官式建筑的柱身的高度较大,并且加上起翘的檐口,其实屋顶有一种脱离大地的态势,这在伍重那张著名的台基屋顶图式中体现得极为分明。因为冯纪忠关注屋顶和大地的关系,所以屋顶形式的变化是与场地深刻地发生关系的。檐口的高低也与四周的环境发生关系,如此以来对人的视线进行有效的控制。何陋轩地处方塔园的东南一隅,东侧和南侧都靠近城市道路,当时在绿化稀疏的状况下,远处的景观并不宜人,对视线的控制是必要的。因此这两侧檐口都有压低,正体现了因地制宜的设计策略(图11)。
图10,方塔园北门剖面图,大屋顶被分解为两片独立的单坡顶
图11,50年代同济大学食堂,竹结构搭建
图12,何陋轩剖面,不对称屋顶的变化和朝向、视线的控制有关
王澍:表现的屋顶
王澍曾经为何陋轩做过一次文献展(),并且他公开声明自己传承了冯纪忠的建筑思想。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让我感兴趣的是,在现代中国建筑史上,冯纪忠先生处于什么特殊的位置。实际上,他是可以被视为一类建筑的发端人……二十几年后,仍然有一些中国建筑师对冯先生的松江方塔园与何陋轩不能忘怀,我以为就在于这组作品的“中国性”。这种“中国性”不是靠表面的形式或符号支撑,而是建筑师对自身的“中国性”抱有强烈的意识,这种意识不止是似是而非的说法,而是一直贯彻到建造的细枝末节。以方塔园作为大的群体规划,以何陋轩作为建筑的基本类型,这组建筑的完成质量和深度,使得“中国性”的建筑第一次获得了比“西方现代建筑”更加明确的含义[13]。
王澍似乎有意建构一个传统,一个传承的脉络,即某“一类建筑”,这个传统起始于30年前的何陋轩,而王澍自视为这一个传统的传承人。从方塔园到象山中国美院,从冯纪忠到王澍,他暗示了一种线形的传承发展。30年,正好是改革开放的30年,这条路线以中国建筑师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作为一个里程碑。为这“一类建筑”,王澍甚至创造了一个词——“中国性”。王澍是深怀历史意识的建筑师,他当然了解梁思成问题:“我想起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序中的悲愤,疾呼中国建筑将亡……”[14]。不过他否定以往那种模仿式的传承,而认为何陋轩更体现了一种建筑语言上的突破;在他看来,如梁思成那般维持对历史建筑的结构体系的再现是不必要的,只有废除了屋顶下粗大的梁柱体系,才能彻底颠覆传统建筑语言。换言之,梁思成所追求的历史建筑中“豪劲”的结构表现,恰恰成为王澍意图抛弃的事物。
宁波五散房的展厅()在功能和尺度上都与何陋轩非常类似的,基地都同样面临着一片水面。屋顶采用了两波起伏的坡屋顶,使它获得了一个标志性的立面。这种屋顶形式在其他项目中也一再使用,俨然成为一种“中国性”风格的标志,被广为传抄。但是这个屋顶形式的操作看起来似乎没有和基地发生密切的关系。室外的地坪被处理成完全的平整。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他的前辈在处理屋顶的变化时与地形建立的微妙关系。虽然王澍在同济攻读博士学位时,一定对葛如亮和冯纪忠的作品有相当的了解。五散房富有表现力的屋面曲线似乎仅仅是对吴冠中式民居绘画中线条的转译,是写意的又是任性的。屋顶内部是无梁混凝土的曲面板,显示了一种禁欲主义的光洁趣味。屋顶的结构性表达被消弭了,而成为更为抽象的板片形式。有趣的是,展厅的东侧地坪有着轻微的倾斜,这在北立面上也显示出来,仅仅在此,这轻微的动作与起伏的屋顶有一种呼应关系(图13,14)。在建筑内部,建筑师赋予形式一个逻辑上的理由。
汉宝德认为屋顶的曲线是中国建筑的最根本的特征,而不是附属的特征。以往的建筑史家(如梁思成)从结构理性和功能的角度来解释屋檐的曲线,汉宝德认为都是多余的,他认为屋顶是中国传统气韵(生动)文化的产物,屋面曲线具有文化意义。曲线屋面就是他觉得最有中国特色的形式,舍此则别无特征更有韵味[15]。如此,汉宝德对五散房展厅的处理或许会十分同意。
五散房的屋顶,常常被误读为所谓“中国性”的特征。但是它已经远离了以往的象征性观念,以及结构性的呈现,而作为一种纯粹的表现形式;同样,它也没有80年代那些屋顶变形与基地环境结合的特征,而几乎是建筑师建立其个人独特性的自由表现。这种趋势在中国美院象山校区达到高峰,直到最近才有另外一个转向,例如象山校区的“瓦山”,又回到了屋顶的结构性表现。
图13,五散房南立面,自由的曲面屋顶
图14,五散房北立面,从外部可以看出东侧室内地坪有轻微的倾斜
结语:大屋顶从象征到表现的变迁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16]。如果历史没有勾起当下的兴趣,没有引发当下的思考,那么,它就只是一堆静止的文献和文物,芜杂而没有生命力。作为一种设计资源,历史并不是现成可用的,它可能是启示,也可能是枷锁,只有当思考这一历史的建筑师加入了自我的心灵意识或生命体验时才能使之复活与再生,并且打下时代的烙印。
梁思成的历史写作引入了结构理性主义思想,作为分析历史建筑的结构合理性的依据,并据此判断建筑的历史价值[17]。梁思成以他强有力的叙述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价值系统,虽然他没有言明这是唯一正统。但是这种反复叙述本身就暗示了,庙堂、宫殿建筑是中国历史建筑的精华;大屋顶是传统价值的最鲜明的体现,最完美的体现在唐或辽的历史遗迹中。古典主义的思想就是要发现和回归到到古老的价值系统;正如儒家学者不断地阐释经典,强调经典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实践的目标就是为了重返经典的价值。梁思成的复古行动恰恰反映了他具有文艺复兴式的使命感,即身处中国历史上最为羸弱的时代,期盼着复兴黄金时代的“豪劲”与活力。
80年代是建筑实践者个人身份的建立和批判性起步的时代。这一时期,建筑师个体的自我意识已经在苏醒,个人的创造性逐渐得到肯定,观察历史、文化的视角从国家-民族视角向个人视角转变,在宏观的“大我”中开始凸现具体的 “小我”。建筑实践在集体性的追求中也显示出个体性的文化选择。葛如亮认为,建筑师的主观意图是作品成败的关键,“一个建筑作品……是看作者,看他的思想和表达方式,看他对各种客观事物的理解和矛盾的处理。主观来源于客观,客观则是通过创作者主观来实现……建筑需要个性,是正常的要求……建筑的个性反映着建筑创作者的个性” [18]。如此明确地提出建筑要表达创作者的个性,而不再标榜一种抽象的“民族特征”,着在80年代并不多见,它意味着对以往那些陈词滥调的抛弃。尽管唯物主义的思想仍在——主观来源于客观,即认为人的思想是对外在世界的反映,是客观世界的“镜子”;但是葛如亮并不满足,他要求个性的表现,创作者不仅仅是现实的镜子,他还是“发光体”,建筑形式可以是个人内在精神和气质的表达。而这对于王澍一代,更是不言自明的。
假如说梁思成对待历史是“与古为徒”,在某种程度上约束了个人革新,那么冯纪忠的“与古为新”,就是鼓励将历史作为创新的资源[19]。50年代追求统一的整体的民族性已受到质疑;传统建筑只是作为一种中性的历史资源,而非完美的经典、或永恒价值的载体。历史作为一种设计资源时,其运用将依据个人的经验而非外在的法则,其选择和应用的方向依赖于实践者自身所具有的批判性。当下对历史的阐释是站在当代的、现代主义的角度,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例如归纳出一些设计手法)看待历史。对形式和手法采取拿来主义,往往剥离了其背后的文化和象征的意义。
在几代建筑师的手中,大屋顶不断地被重新诠释:从官式的到民间的;从规则的到不规则的;从结构性的到板片状的;从民族形式的象征到个人性的表现;在变化的屋顶中,既包含了建筑师个人的思考,又体现了时代的变迁。可以确定的是,大屋顶的变形还会继续下去。
注释
[1]《中国建筑的特征》,梁思成著,《凝动的音乐》,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4月,第222-228页。
[2]梁思成是该项目的顾问设计师,并主导了辽代风格的实现,参见赖德霖文《设计一座理想的中国风格的现代建筑》。赖德霖著,《走进建筑,走进建筑史——赖德霖自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0月,第82-121页。另参见龚良《刘敦桢先生与南京博物院》,刘敦桢也是本项目的顾问之一,并于52年重新设计完成了琉璃瓦顶。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编,《刘敦桢诞生110周年中国建筑史学史研究论文集》,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1月,第50-53页。
[3]参见赖德霖文《设计一座理想的中国风格的现代建筑》。赖德霖著,《走进建筑,走进建筑史——赖德霖自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0月,第82-121页。
[4]豪劲、醇和、羁直对应英文中的vigor,elegance, rigidity。梁思成英文原著,费慰梅编,梁从诫译,《图像中国建筑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
[5]该文是《中国建筑史》的一篇序言。梁思成著,《凝动的音乐》,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4月,第209页。
[6] 参见戴念慈文《回忆梁公》。张祖刚主编,《当代中国建筑大师——戴念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年,第169页。
[7] 参见戴念慈文《论新中国的建筑及其他》,《谎》是其中一则评论,文章大约写于1949-1951年间。《当代中国建筑大师——戴念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年,第240页
[8]同上,第230页。
[9]参见1964年3月22日《致车专员信——湛江湖光阁设计意见》,梁思成认为清代官式建筑风格不宜用在南方,建议“要富于地方风格和民间气息要给人亲切感,要凭平易近人…”。梁思成著,《凝动的音乐》,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4月,第382-386页。
[10] 葛如亮著,《葛如亮建筑艺术》,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43页。
[11]同上。
[12]参见《何陋轩答客问》。冯纪忠著,《与古为新——方塔园规划》,北京,东方出版社, ,第134页。
[13]王澍《小题大做》,该文刊发于《新观察》建筑批评专栏第7辑:“何陋轩论”笔谈。《城市空间 设计》杂志[J],北京,《艺术与设计》杂志社, 第5期。
[14]同上。
[15]汉宝德著,《中国建筑文化讲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月,第37页。
[16][意]贝内德托・克罗齐著,田时纲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7] 参见赖德霖文《设计一座理想的中国风格的现代建筑》。赖德霖著,《走进建筑,走进建筑史——赖德霖自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0月,第82-121页。
[18]同注[10],第150-153页。
[19]“与古为徒”,语出《庄子·人世间》,喻尚友古人。冯纪忠“与古为新”应是化庄子之语而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