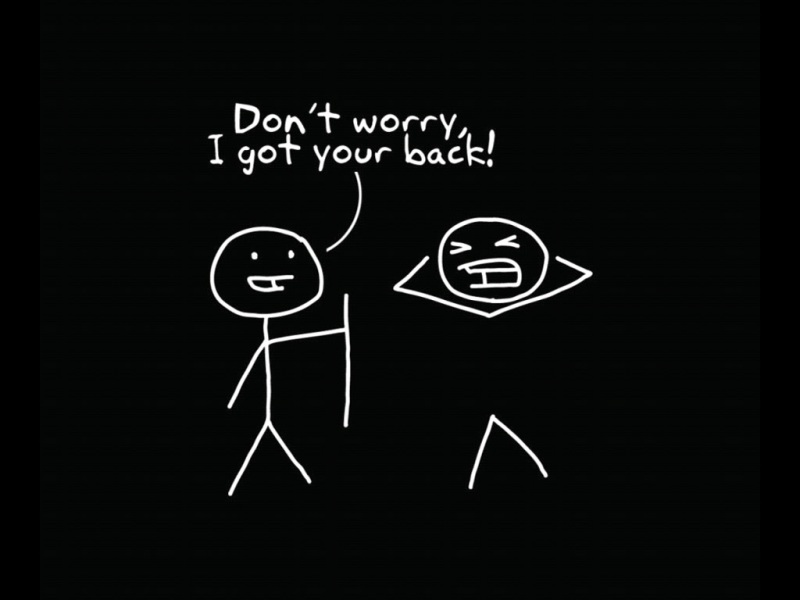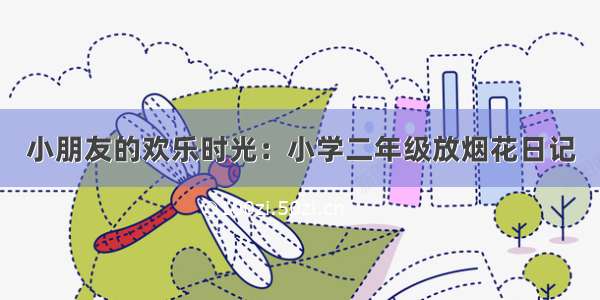▲同写意15周年千人大会——分会三“细胞免疫治疗:药物干预新纪元”,邀请了全球细胞免疫治疗重量级研究学者、临床一线KOL、领先企业CEO及首席科学家,献策实体瘤等难点如何攻克。
作者 / Timbersaw
以PD-(L)1单抗为代表的第一代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B)在多数肿瘤仅有不到20%的有效率,因而近几年来,如何通过药物联用提高ICB有效率,解决免疫疗法耐药问题,成为了学术界和制药界的研究热点。
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有数千个联用方案进入临床试验,以期为第一代ICB寻找各式各样的‘理想搭档’。
联用药物从作用对象上讲,可以针对肿瘤细胞本身,肿瘤微环境(TME)的各类成分等;
从靶点机理上讲,可以针对VEGFR、STING、PARP、CD47、LAG-3、4-1BB、TGF-β、IDO、CSF1R、CD73等靶标;
从药物类型上讲,可以是放化疗、小分子、大分子、细胞疗法、溶瘤病毒、疫苗、核酸、甚至是微生物组分、外泌体等。
已有的临床数据显示,化疗、VEGFR拮抗剂、溶瘤病毒、PARP抑制剂等药物联用ICB展现了较为积极的疗效(或初步疗效),部分联用方案已获FDA批准针对特定肿瘤,而LAG-3、CSF1R、IDO等联用策略的效果并不理想甚至让人大失所望。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但失败的原因更需要剖析,也许是入组病人的选择、诊断及预后的生物标志物选择、序贯治疗方案的设计、靶点通路的重要性、肿瘤逃逸或对免疫疗法产生耐药性等等因素所致。
业界一直有声音呼吁,临床联用试验应建立在扎实的基础研究之上,少一些急功近利。
笔者支持这种观点,也借本文对免疫疗法耐药,特别是其与TME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希望有助于行业同仁拓宽思路。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将主要从免疫疗法耐药性问题展开,介绍免疫编辑理论(Cancer Immuno-editing)和不同的耐药类型,分析TME的类别以及促进肿瘤逃逸和耐药的主要组分,并探讨相应的药物联用开发进展和未来方向。
01 免疫编辑与免疫疗法耐药
1、免疫编辑在讨论免疫疗法耐药之前,需要引入一个重要概念,即肿瘤的免疫编辑理论(Cancer Immuno-editing)。
根据该理论,癌细胞在机体内的发生、发展是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免疫系统不仅具有清除肿瘤细胞的能力,而且还具有促进肿瘤生长的作用。
免疫编辑共分为三个阶段:清除(Elimination),平衡(Equilibrium),逃逸(Escape)。
清除阶段
固有免疫和特异性免疫协同作用,DC、NK、巨噬细胞、效应T细胞等识别并消灭肿瘤细胞。
平衡阶段
个别的癌细胞克隆因其免疫原性低或其他原因,躲过了清除阶段,肿瘤进入平衡阶段,即肿瘤生长停滞。一般认为主要由特异性免疫维持这个平衡,而固有免疫机制不参与该阶段。
逃逸阶段
癌细胞基因组是非常不稳定的,随着免疫系统持续的选择压力,越来越多的癌细胞克隆拥有了躲避免疫系统识别或消除的能力,如MHC和/或肿瘤抗原肽表达缺失,肿瘤生长逐渐不受控制,最终发病。
图1 肿瘤的免疫编辑理论[1]2、免疫疗法耐药免疫编辑不仅仅发生在自然发展的肿瘤中,临床证据显示,免疫编辑会在ICB治疗过程中再度出现[2]。
因而,免疫疗法耐药既可能由治疗前的肿瘤免疫编辑造成,也可能由治疗过程中或之后出现的免疫编辑导致,这正对应了免疫耐药的两大类别:先天性耐药(Innate resistance)和获得性耐药(Acquired resistance)。
先天性耐药
即ICB对肿瘤无效,可能的原因如患者自身的免疫机能低下(如老年人或AIDS患者);肿瘤的免疫原性较低(如非病毒引发的,突变荷载低的肿瘤);ICB治疗前肿瘤微环境已经演化出了多种免疫抑制机制等。
获得性耐药
即ICB最初对肿瘤有一定效果,但在治疗过程中或之后疾病复发,可能的原因如免疫治疗重塑了肿瘤微环境,从而演变出新的免疫抑制机理;肿瘤在进化压力下衍生出新的耐药突变株(如抗原呈递体系或干扰素受体信号的缺失)等。
图2 肿瘤的免疫编辑(上半部分)与免疫疗法耐药(下半部分)[3]下一代免疫疗法的重点是解决第一代ICB耐药问题,上文提到,无论原发还是继发性耐药,都与肿瘤微环境TME(也有人细化定义为肿瘤免疫微环境,TIME)密切相关,因为免疫编辑导致耐药的过程就是肿瘤与TME中各类细胞、受体、分泌因子、代谢物等动态互作的演化历程。
本文后半部分将主要讨论TME与ICB耐药的相关性,以及靶向TME的药物联用策略。
02 肿瘤微环境(TME)与免疫疗法耐药
肿瘤微环境(TME),即肿瘤细胞产生和生活的内环境,其中不仅包括了肿瘤细胞本身,还有其周围的成纤维细胞、免疫和炎性细胞、胶质细胞等各种细胞,同时也包括附近区域内的细胞间质、微血管以及浸润在其中的生物分子如细胞因子、趋化因子,还有各种代谢产物和理化条件等,它们为肿瘤提供营养和支持。肿瘤细胞与TME的细胞外基质,基质细胞和免疫细胞紧密相互作用,促进慢性炎症和免疫抑制,促血管生成的环境也为隔绝杀伤性T细胞浸润提供了物理屏障。
因此,研究TME的组成、类别及其动态变化过程对于控制癌症和克服免疫疗法耐药非常重要。1、TME的主要组分笔者根据近期多篇重磅综述和研究文献,分类总结了TME中80余种主要组分及其促/抑癌功能(表1),虽不能说十分完整,但也可作为参考。
2、TME的类别为深入分析TME的免疫耐药机理并寻找联用策略,需要对免疫治疗相关的临床病理表型进行分类梳理。近几年很流行的一个理论根据患者的免疫表型将肿瘤分为‘热’肿瘤、‘冷’肿瘤和免疫阻隔型肿瘤三大类[9]。1)‘热’肿瘤(炎性肿瘤,inflamed tumor)的特征如下:肿瘤实质中有大量的免疫细胞浸润,炎性细胞因子高表达,PD-L1高表达,肿瘤基因组不稳定(新抗原neo-antigen表达几率高),TMB高,曾有过抗肿瘤免疫反应(现被肿瘤抑制)等。
免疫‘热’肿瘤一般对ICB治疗的响应程度较高,发生先天性耐药的概率较低。2)‘冷’肿瘤(非炎性肿瘤,non-inflamed tumor,或免疫‘荒漠’,immune-desert tumor)可能的特征如下,肿瘤实质中几乎没有免疫细胞浸润,罕有PD-L1表达,肿瘤基因组稳定,未出现过抗肿瘤免疫反应等。免疫‘冷’肿瘤一般对ICB治疗的响应程度较低,发生先天性耐药的概率较高。3)免疫阻隔型肿瘤(immune-excluded tumor),虽然也可以检测到免疫细胞的激活和扩增,但最关键的浸润(infiltration)过程被肿瘤血管、间质等物理屏障阻隔,导致效应细胞无法发挥作用。该类肿瘤对ICB治疗的响应程度也比较低。
图3 肿瘤的不同免疫表型(棕色:冷肿瘤;蓝色:免疫阻隔型肿瘤;红色:热肿瘤)[9]‘冷热’肿瘤理论现已被广泛认可,也有了定量的指标-免疫评分(immunoscore)。
该指标定量检测肿瘤中心和侵袭性边缘的CD3阳性和CD8阳性淋巴细胞群,评分从I0到I4,代表免疫细胞在上述两个肿瘤区域的密度逐渐增加[10]。免疫评分已在结直肠癌(CRC)和黑色素瘤等肿瘤类别中展示了良好的诊疗及预后价值。在初NatureReviews Drug Discovery的一篇综述上,研究人员对‘冷热’肿瘤理论进一步补充完善,新增描述了一类免疫抑制型(immuno-suppressed)肿瘤,这一类别没有被物理屏障限制,但由于一众免疫抑制机理的存在,仅有少量的免疫效应细胞(CD8+ T)浸润,且无法进一步招募或扩增这类细胞[11]。
文章将这一类型与上文提及的免疫阻隔型肿瘤合并为一类,称作免疫改变型‘immune-altered’肿瘤(图4a)。
图4 以免疫评分定义免疫‘热’肿瘤,‘改变型’肿瘤和‘冷’肿瘤[11]上述四种免疫表型所代表的TME,在免疫细胞浸润、肿瘤血管/基质结构、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分泌、肿瘤自身免疫原性等方面有较大差别,因而对ICB产生耐药的概率和机理也有所不同,需要分别采取对应的联用方案克服耐药,下一章节‘靶向TME的联合疗法’详细介绍。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不同组织来源的肿瘤,因组织器官的组成结构、功能、内外环境因素和发病机制等差异,其TME是不尽相同的,这一点在设计靶向策略时也要注意。
但为避免文章内容涉及过多维度,干扰读者理解要点,这部分本文不深入展开,感兴趣可参考Nature Reviews Cancer的一篇综述[12]。
03 靶向TME的联合疗法
如前所述,不同类型的肿瘤TME对ICB的响应率和耐药机理是不同的,因而采取针对性的联用策略,体现了‘精准医学’的理念。
图5 不同免疫类型肿瘤的特征、治疗靶点和联用策略[11]1、免疫‘热’肿瘤的联合疗法免疫‘热’肿瘤有较多的免疫细胞(尤其是CD8+T细胞)浸润,因此ICB针对这类肿瘤的疗效较好。
但还是会有耐药情况的出现,可能是T细胞表达了其他的抑制性免疫检查点如LAG-3、TIM3、TIGIT、BTLA、VISTA等而一直处于失能/耐受状态。
全球众多企业针对这些新靶点开发了治疗性抗体,虽然临床前数据优异,但早期临床表现不是十分理想,单药应答率较低,与PD-1抗体联用的疗效也没有大幅提升。
LAG3抗体
全球临床(13个)加研发阶段(22个)共35个项目。BMS的relatlimab处于全球II/III期临床,进展最快。
在前期小规模试验中联合O药,用于PD-1/PD-L1抗体治疗耐药或者失败的恶性黑色素瘤患者。
结果显示:48名疗效可评估的患者中,6位患者肿瘤明显缩小,有效率为12.5%;对于LAG-3表达量大于1%的25位患者来说,有效率20%;对于LAG-3表达量小于1%的患者,有效率只有7.1%。
而MSD的LAG3单抗MK-4280针对治疗失败的各种实体瘤,入组33例患者,其中18人接受MK-4280治疗,15人接受MK-4280+K药联合疗法。
结果显示:单药治疗组,1名患者肿瘤明显缩小,有效率6%,疾病控制率为17%;联合治疗组,4名患者肿瘤明显缩小,有效率为27%,控制率为40%。另外,LAG3靶点药物相关的不良反应也值得关注。
TIM3抗体
全球临床(10个)加研发阶段(14个)共24个项目。Tesaro的cobolimab,Novartis的MBG-453,BMS的BMS-986258均处于II期临床。
Eli Lilly在Q2业绩报告中将一款处于I期的PD-L1/TIM-3双特异性抗体(LY-3415244)从pipeline中剔除,但仍保留处于I期的TIM-3单抗(LY-3321367)。
TIGIT抗体
全球临床(6个)加研发阶段(16个)共22个项目。BMS的BMS-986207,Genentech的tiragolumab处于II期临床。
MSD的TIGIT单抗MK-7684在I期临床用于标准治疗方案失败的晚期实体瘤,共入组68例患者,其中34例接受MK-7684单药,34例接受MK-7684+K药联用。
结果表明:单药组中观察到1例部分缓解(3%,n=1/34),联用组有8例(19%,n=8/43)。单药组和联合组的疾病控制率分别为35%和47%。除了给T细胞‘松多个刹车’,也可进一步‘踩油门’克服耐药,即使用激动性抗体调节免疫激活型靶点,如4-1BB,ICOS,GITR,OX40,CD27等,详情可参考笔者之前写过的文章:免疫激动性抗体的机遇与挑战。
结合今年以来的研究进展,笔者认为目前该方向的药物在疗效上仍需有较大突破,另外,如何有效管理免疫过度激活引起的不良反应也是一个关键点。2、免疫‘改变型’肿瘤的联合疗法前面提到,免疫‘改变型’肿瘤分为免疫抑制型和免疫阻隔型两类。为了便于理解,将这两个类型分开来讲。但须注意的是,有一些耐药机理可能是跨类型的,只是重要程度的区别。1)免疫抑制型的TME仅有少量的效应T细胞浸润,存在抑制性的免疫或非免疫细胞(如MDSC、TAM、Treg、CAF等)、分泌因子(如IL-10、TGF-β等)、代谢产物(如犬尿氨酸),也可能T细胞表达了其他的抑制性免疫检查点等。2)免疫阻隔型的TME由于肿瘤血管/间质的物理屏障,导致T细胞聚集在肿瘤侵袭边缘,没有T细胞浸润到瘤床(tumor bed),存在抑制性的代谢产物(如腺苷)、理化环境(如低氧)等。根据它们不同的特点,联用疗法也需‘对症下药’。
针对免疫抑制型肿瘤
1)靶向抑制性分泌因子抑制性的分泌因子(如细胞因子、生长因子)是抑制性TME的重要诱因,如最常被提及的IL-10和TGF-β。
根据肿瘤类型、肿瘤发展阶段、肿瘤微环境等的不同,IL-10和TGF-β都可能会出现抑癌和促癌的双面功能,因此早前作为治疗靶点并不被看好。
但是,德国Merck的PD-L1/TGF-β双功能融合蛋白bintrafusp alfa(M7824)在临床试验中展现了很好的治疗潜力,二线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I期临床,对于PD-L1>1%的患者群,ORR为40.7%(n=11/27);对于PD-L1≥80%的强阳性患者,ORR高达71.4%(n=5/7)。
2月,Merck与GSK达成总额高达37亿欧元的合作,共同负责M7824在全球范围内的临床开发及商业推广。国内方面,恒瑞开发了PD-L1/TGF-β双抗SHR-1701,目前处于I期临床。2)靶向免疫抑制性细胞免疫抑制性细胞主要指Treg、MDSC、M2型TAM等。
Treg
一般主要指Foxp3+Tregs,在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Treg通过分泌某些抑制性细胞因子(如IL-10,IL-35和TGF-β)或直接接触细胞抑制效应T细胞应答,促进肿瘤逃避和抵抗免疫反应。
目前靶向Treg的联用策略,其侧重点在于如何提高Teff(效应T细胞)/Treg的比例,寻找能够有偏向性地激活Teff而不激活Treg,或偏向性地抑制Treg而不抑制Teff的药物或技术。Nektar therapeutics的PEG改造型、CD122偏向性IL-2激动剂Bempegaldesleukin(NKTR-214,bempeg),能够偏向性激活CD8+Teff而非Treg,不仅在临床前小鼠模型显示显著疗效,在与PD-1单抗Opdivo联用的临床试验中,也对黑色素癌、肾细胞癌等多种肿瘤显示优异的ORR,多个适应症的联用疗法已进入III期临床。
FDA近期授予上述联用疗法针对黑色素瘤的BTD资格,另外加上BMS高达36亿美金的合作背书,这一联用方案成功上市应该只是时间问题。免疫激动性检查点GITR,是肿瘤坏死因子受体超家族的一员,在Treg表面的表达量很高,在Teff表面也有表达。GITR通路在Treg和Teff中的功能不尽相同,GITR与GITRL的结合可以抑制Treg活力,而同时刺激Teff,因此对于ICB而言,是比较有潜力的联用策略。
但从目前GITR激动性抗体的临床数据看,单药疗效似乎比较一般,Amgen已终止了其GITR项目AMG228。Leap Therapeutics的GITR单抗TRX518与PD-1单抗的联用临床值得关注(NCT02628574),以Treg的细胞活性作为替代性的生物标志物看起来也是必要的。
MDSC
MDSC是骨髓来源的一群异质性细胞,是树突状细胞(DCs)、巨噬细胞和(或)粒细胞的前体,具有显著抑制免疫细胞应答的能力。通过靶向抑制性代谢通路(如IDO、精氨酸、色氨酸、NO等)调控MDSC本来是十分有潜力的联用策略,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类机理尤其是IDO,受到较多质疑。PI3K-γ亚基在髓系细胞高表达,临床前研究显示,PI3K-γ抑制剂有与ICB联用的潜力。
目前,Infinity Pharmaceuticals的选择性PI3K-γ抑制剂IPI-549与O药联用的I期临床正在进行中(NCT02637531)。
TAM
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是肿瘤微环境中血管生成,侵袭,转移以及肿瘤基质中免疫抑制性的主要调节因子。
TAM分两种类型,M1型抑制肿瘤,M2型促进肿瘤。因此,如何特异性减少M2型成为靶向TAM的关键。临床前研究显示,阻断集落刺激因子1受体(CSF-1R)信号能够特异性去除M2型TAM,有与ICB联用的潜力。
11月,Five Prime公布了CSF1R抗体cabiralizumab联用O药二线治疗胰腺癌的部分结果,ORR为10%,但43%的患者发生3-5级不良反应。罗氏的CSF1R抗体emactuzumab与PD-L1单抗T药(atezolizumab)联用的临床目前处于I期。
除了抗体外,临床阶段也有多个CSF-1R选择性小分子抑制剂与ICB联用,比如Array BioPharma的ARRY-382,在与K药联用治疗晚期实体瘤的Ib期试验,显示PR为11%(n=2/19),目前II期临床正在进行中。另外需要说明的是,CD47、CD24等靶标的机理虽然也涉及巨噬细胞,但与本文所讨论的话题有一定区别,所以对其进展和竞争态势不做过多分析,业内也已有很多文章详细讨论。
笔者个人观点:如能管理好血小板相关副作用,CD47单药及联用rituximab等的前景是很不错的;而如果没有更充分的数据支持,CD47抗体与ICB的联用更像是1+1≤2(而非1+1>2)。
调节固有免疫反应
这其实就是常说的‘踩油门’策略,不仅可以针对免疫抑制型肿瘤,也可针对‘冷’肿瘤。
cGAS-STING通路也是近几年的研究热门,STING全称Stimulator of Interferon genes(干扰素刺激基因),是固有免疫系统的组分。
STING能够识别胞质的外源DNA,激活之后能够增加干扰素以及细胞因子的生成,并通过一系列的级联反应,激活适应性免疫系统,活化T细胞。
然而STING激动剂的临床进展似乎不太顺利。ESMO,MSD公布,STING激动剂MK-1454治疗黑色素瘤单药没有应答,加上K药有小于30%的ORR。
ASCO,Aduro公布STING激动剂ADU-S100和Novartis的PD-1单抗Spartalizumab联用治疗晚期实体瘤数据,ORR不足10%(n=5/53)。TLR(Toll样受体)是非常重要的固有免疫受体,TLR可以识别病原相关分子模式(PAMP)和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导致固有免疫细胞激活,进而分泌促炎症细胞因子及启动特异性免疫。TLR激动剂的临床进展值得关注。
AACR,Checkmate Pharmaceuticals公布的Ib期数据显示,TLR9激动剂CMP-001与K药联用在晚期黑色素瘤患者中的ORR达到22%(n=15/69),显著高于K药单药的历史数据。目前II期临床正在进行中。
针对免疫阻隔型肿瘤
1)调控T细胞迁移相关趋化因子免疫阻隔型TME的成因很多,可能是某些与T细胞招募相关的趋化因子如CXCL9、CXCL10、CXCL11、CXCL13、CX3CL1、CCL2、CCL5等缺失,而这些趋化因子缺失的诱因可能是致癌突变、遗传和表观遗传通路失调等。
因此潜在的策略是,直接用能促进效应T细胞向肿瘤富集的趋化因子治疗,或通过表观遗传药物选择性调控‘有益’的趋化因子(如CXCL9、CXCL10)表达。2)打破物理屏障肿瘤血管和细胞外基质成分也会导致免疫细胞无法浸润肿瘤,VEGF/VEGFR抑制剂与ICB的联用策略已经证实有效。
12月,FDA批准罗氏的PD-L1单抗Tecentriq(atezolizumab)联合Avastin(贝伐珠单抗)、化疗(紫杉醇和卡铂)用于一线治疗无EGFR或ALK突变的转移性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NSCLC)。
4月,FDA批准K药联合Inlyta(axitinib,阿西替尼)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肾细胞癌。
5月,FDA批准辉瑞/德国默克的PD-L1单抗Bavencio(avelumab)与阿西替尼联合用于晚期肾细胞癌(RCC)患者的一线治疗。
K药+仑伐替尼三次获得FDA的BTD资格(1月,肾癌,客观缓解率70%,控制率96.7%;7月,子宫内膜癌,客观缓解率47.2%,疾病控制率83%;7月,肝癌,客观缓解率42.3%,疾病控制率100%)。3)克服低氧相关免疫抑制低氧(hypoxia)是肿瘤微环境的重要特点,低氧导致低氧诱导因子HIF(主要是HIF-1α和HIF-2α)稳定表达。
HIF作为转录因子,广泛调控基因表达,增加微血管生成、促进细胞增生、分化,与抑制性肿瘤微环境的形成和发展关系密切。
HIF-1α可以促进PD-L1和VEGF表达,因此靶向HIF理论上可与ICB产生协同效应,不过目前基本没有特异性的HIF-1α抑制剂进入临床研究,而Peloton Therapeutics开发了一款HIF-2α抑制剂PT-2977,将于开始肾癌三期临床。
5月,MSD宣布将以10.5亿首付、11.5亿里程金共计22亿美元收购Peloton Therapeutics,表明其对于K药联用HIF-2α抑制剂的组合在相关适应症前景的认可。HIF-1α还可以增强腺苷(adenosine)信号,后者通过下游的A2aR受体信号,激活免疫抑制型细胞,同时抑制免疫效应细胞。
因此,抑制腺苷信号通路的CD39/CD73/A2aR等分子,同样有与ICB联用的潜力。目前全球范围内,临床阶段的CD39抗体只有一个(I期),即TizonaTherapeutics的TTX-030。
1月,AbbVie与Tizona达成合作,共同开发和推广靶向CD39的癌症疗法。
目前有6个CD73抗体处于临床阶段,BMS的BMS-986179和AZ/MedImmune的oleclumab处于II期临床,早期数据显示,不论CD73单抗与PD-1或PD-L1单抗联用,客观缓解率约在10%左右,还需进一步期待更多更优的数据,详情可参考笔者之前的文章:肿瘤免疫新兴靶点之:CD73。
目前有6个A2aR小分子抑制剂项目处于临床阶段,其中Novartis、AZ、Corvus、MSD的项目都在II期,但整体来看,该方向进展较慢,且疗效数据比较一般。3、免疫‘冷’肿瘤的联合疗法免疫‘冷’肿瘤基本没有T细胞浸润,且由于肿瘤较低的免疫原型,不能有效激活特异性免疫,同时肿瘤本身对T细胞的杀伤作用也不敏感,属于顽疾,预后较差。
目前针对‘冷’肿瘤的策略重点是如何将其调‘热’,即增强炎症性免疫反应,促进效应T细胞浸润、激活和增殖。
可以通过放化疗、溶瘤病毒等促进肿瘤细胞抗原的释放,用疫苗促进抗原呈递和T细胞激活,使用激活型抗体靶向免疫激动性靶点(前文已介绍),用IL2、IL7、IL15、IL21、GM-CSF等细胞因子促进效应T细胞扩增,也可直接采用TIL细胞疗法。
图6 免疫‘冷’肿瘤的治疗策略[11]1)联用化疗蒽环类、环磷酰胺、奥沙利铂和紫杉烷类化疗药物能够引发肿瘤的免疫原性细胞死亡(ICD),释放DAMPs,并通过DC等APC致敏效应T细胞,激发免疫反应。
化疗联合ICB的疗效已经得到确证。5月,FDA加速批准化疗与K药联用,一线治疗转移性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NSCLC),K药联合化疗的有效率是55%,单独化疗的有效率是29%,联合治疗能降低47%的疾病进展风险。
8月,FDA批准K药与培美曲塞和铂类化疗联用,在无EGFR和ALK癌症基因变异的患者中,一线治疗转移性非鳞状NSCLC。
10月,FDA批准K药与标准化疗(卡铂、紫杉醇/白蛋白紫杉醇)联用,一线治疗鳞状NSCLC。2)联用溶瘤病毒溶瘤病毒(OV)也是近几年的热门领域,其优势在于,通过基因工程手段减毒增效,OV能够选择性裂解肿瘤细胞,调节TME,系统性地增强固有免疫和获得性免疫,与ICB联用有很大潜力。
Talimogene laherparepvec(T- VEC)是FDA批准的第一款溶瘤病毒,在一项针对晚期黑色素瘤的Ib期研究中,T-VEC联合K药获得了高达62%的ORR[13]。
目前还有其他近十种OV与ICB联用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试验编号以及关于OV技术更详细的情况可参考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最新一篇综述[14]。3)联用疫苗理论上讲,肿瘤疫苗能够通过抗原呈递系统有效激活免疫反应并形成免疫记忆,但早期的临床结果令人失望,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疫苗无法逆转肿瘤中已存在的免疫抑制。
因此,与ICB联用应当是不错的选择。肿瘤疫苗的类型多种多样,可以是DNA、RNA、多肽、细胞或者基因工程微生物等。
相比于之前的肿瘤相关抗原(TAA),现在肿瘤疫苗的研究热点是肿瘤特异性抗原(TSA)或新抗原(neo-antigen),neo-antigen疫苗理论上能够减少副作用,实现个体化医疗。
NeonTherapeutics是一家专注neo-antigen疫苗的公司,其科学创始人之一Catherine Wu已在Nature上发表了多篇关于该类疫苗治疗黑色素瘤和胶质瘤的临床研究文章。
该公司的个体化新抗原疫苗候选产品NEO-PV-01联合O药,在治疗晚期或转移性黑色素瘤、吸烟相关NSCLC、膀胱癌的Ib期临床取得了不错的初步疗效(ORR分别为47%,22%,24%)。
笔者认为neo-antigen疫苗联用ICB的治疗前景很值得期待,而相关的成本和生产效率等问题也需要关注。4)联用DNA损伤修复通路抑制剂说到DNA损伤修复(DDR)通路,不能不提聚腺苷酸二磷酸核糖转移酶(PARP)。已有多款小分子PARP抑制剂获批治疗卵巢癌,另外还有十几种肿瘤适应症在研。
7月,MSD和AZ开展了K药联用PARP抑制剂olaparib的大型合作。8月,BMS也与Clovis达成合作,开发O药与PARP抑制剂rucaparib的联合疗法。
6月,JAMA Oncol的一片文章显示,K药联用PARP1/2抑制剂niraparib治疗转移性TNBC的II期临床中,ORR达到21%。
另有临床前研究显示, PARP抑制剂或CHK1抑制剂可以显著增加PD-L1表达,还可以激活STING通路,从而增强ICB的疗效。除了PARP,DDR通路的其他分子,如ATR、ATM、CHK1、MK2等的抑制剂与ICB联用的临床进展也值得关注。5)联用细胞因子细胞因子方面,前文已提到Nektar的改良型IL-2药物,此处不再赘述。
IL-15近期获得了较大关注,其优势在于没有IL-2药物相关副作用,且不激活Treg。
ALT-803是一款IL-15超激动剂,在一项与O药联用治疗NSCLC的Ib期临床中,在少量病人中的ORR达到27%(n=3/11),DCR达到91(n=10/11),目前II期临床正在进行中。
另外,2月,Genentech与Xencor达成合作协议,共同开发新型IL-15细胞因子疗法。6)TIL细胞疗法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疗法已有二十多年历史,但早期的进展并不快,应用也不广泛。
最近几年,随着CAR-T的兴起,TIL疗法也获得了较大关注。
ASCO,Iovance Biotherapeutics公布的研究数据显示,在ICB治疗失败的黑色素瘤患者中,其TIL疗法LN-145的有效率为38%(n=21/55),其中包括2名患者肿瘤完全缓解、19名患者肿瘤明显缩小,疾病控制率为76%。
这一结果显示了TIL克服ICB耐药的潜力,值得关注。4、生物标志物辅助联合疗法开发用于诊断、用药、预后的生物标志物对于解决耐药问题及提高ICB疗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PD-L1表达水平、MSI(微卫星不稳定性)、TMB(肿瘤突变负荷)、ImmunoScore(免疫评分)等都常用于辅助免疫疗法实施,很多药企也在针对内部项目开发临床生物标志物。
由于肿瘤在治疗方案的选择压力下会不断演化新的免疫抑制机理,因此对于获得性耐药,我们可能更需要伴随诊断,在治疗过程中定期检测各种指标,对比基线水平,寻找可能的耐药机理,并设计应对策略。
图7 动态分析肿瘤治疗过程中各种指标的变化[15]要点总结:第一代ICB的有效率亟待提高,免疫疗法耐药与免疫编辑过程密切相关。
肿瘤微环境(TME)促进了各种免疫耐药机理的发生发展。
针对TME的不同类型,需采取不同的药物联用策略。
开发更有效的诊断及预后生物标志物有助于提高联用策略疗效。
参考资料
1.Schreiber R D, Old L J, Smyth M J. Cancer immunoediting: integrating immunity’s roles in cancer suppression and promotion[J]. Science, , 331(6024): 1565-1570.
2.Yuan J, Page D B, Ku G Y, et al. Correlation of clinical and immunological data in a metastatic melanoma patient with heterogeneous tumor responses to ipilimumab therapy[J]. Cancer Immunity Archive, , 10(1): 1.
3.O’Donnell J S, Teng M W L, Smyth M J. Cancer immunoediting and resistance to T cell-based immunotherapy[J]. Nature reviews Clinical oncology, (16): 151-167.
4.Balkwill F R, Capasso M, Hagemann T. The tumor microenvironment at a glance[J]. , 125(23):5591-5596.
5.Altorki N K, Markowitz G J, Gao D, et al. The lung microenvironment: an important regulator of tumour growth and metastasis[J]. Nature Reviews Cancer, , 19(1):9-31.
6.Li X, Wenes M, Romero P, et al. Navigating metabolic pathways to enhance antitumour immunity and immunotherapy[J]. Nature Reviews Clinical Oncology, : 16(7):425-441.
7.Hinshaw D C, Shevde L A. The Tumor Microenvironment Innately Modulates Cancer Progression[J]. Cancer research, .
8. 肿瘤免疫检查点治疗“拦路虎”之肿瘤微环境篇。医脉通。-03-19
9.Chen D S, Mellman I. Elements of cancer immunity and the cancer–immune set point[J]. Nature, , 541(7637): 321.
10.Galon J, Mlecnik B, Bindea G, et al. Toward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Immunoscore’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malignant tumours[J]. The Journal of pathology, , 232(2): 199-209.
11.Galon J, Bruni D. Approaches to treat immune hot, altered and cold tumours with combination immunotherapies[J]. 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 , 18(3):197-218..
12.Salmon H, Remark R, Gnjatic S, et al. Host tissue determinants of tumour immunity[J]. Nature Reviews Cancer, ,19(4):215-227.
13.Ribas A, Dummer R, Puzanov I, et al. Oncolytic virotherapy promotes intratumoral T cell infiltration and improves anti-PD-1 immunotherapy[J]. Cell, , 170(6): 1109-1119. e10.
14.Harrington K, Freeman D J, Kelly B, et al. Optimizing oncolytic virotherapy in cancer treatment[J]. 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 : 1.
15.Sharma P, Hu-Lieskovan S, Wargo J A, et al. Primary, adaptive, and acquired resistance to cancer immunotherapy[J]. Cell, , 168(4): 707-723.
转载声明:
转载声明:本文经「生物制药小编」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