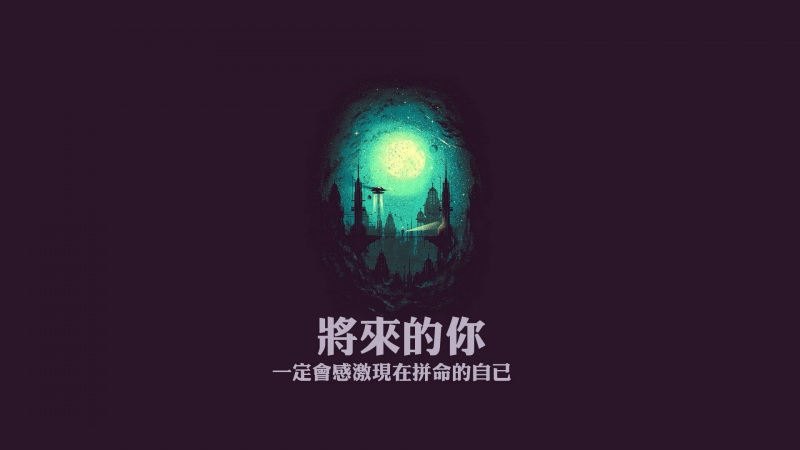广义夏文化指的是夏王朝文化,狭义夏文化则指夏后氏的文化。在当前的夏文化研究中,研究者常常忽视和模糊了夏文化的族属主体,混淆了广义和狭义层面的夏文化,由此造成了概念和认识上的混乱。对于“夏文化”内涵的理解,又进一步关系到探索夏文化的方法论问题。研究夏文化的方法,主要有都邑推定法和文化比较法两种。以文化比较法为基础,从时间、空间和文化面貌三方面综合分析,可知龙山时期“禹域”内第一核心区的王湾类型和煤山类型的晚期阶段系狭义的夏文化,而第二和第三核心区内的诸考古学遗存的晚期阶段则可归入广义夏文化范畴;二里头文化在主体上应属于夏文化。由此,河南龙山文化的煤山类型、王湾类型和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共同组成了完整的狭义夏文化。
*文章原载《中国文化研究》(秋之卷)“夏文化研究专题”,转载自三联学术通讯(ID:sdx_bulletin)。
界说与方法
——夏代信史考古学重建的途径
文 | 孙庆伟
过去数十年的考古实践表明,学术界对于夏文化的认识不但没有形成共识,反而有渐行渐远的趋势,甚至有学者开始怀疑历史上夏代是否真的存在。毫无疑问,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探索夏文化的方法出现了偏差。早在1979年,邹衡先生就语重心长地指出:
在古代文献记载中所见夏商两族活动范围内即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已经不太可能再发现什么新的考古学文化了。同时,因为夏朝同商朝一样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必然就包含在这一空间和这一时间已经发现的诸文化诸类型的各期段之中。我们说,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邹先生其实是在告诫我们,探索夏文化,“方法”远比“发现”重要。本文即着眼于夏文化的界说与探索夏文化的方法,拟对夏代信史考古学重建的途径作进一步的总结与反思。
一、考古学视野中的夏文化
夏文化是一个考古学概念,它与一般所说的夏代文化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目前学术界对于“夏文化”内涵的理解尚有分歧,这又进一步关系到探索夏文化的方法论问题。
徐旭生先生在动身前往豫西“夏墟”调查之前,对于夏文化的内涵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他说:
想解决夏文化的问题还需要指明这个词可能包括两个不同的涵义。上面所说的夏文化全是从时间来看,所指的是夏代的文化。可是从前的人相信我国自炎黄以来就是统一的,我们却不敢附和,我们相信在夏代,氏族社会虽已到了末期,而氏族却还有很大的势力,中国远不是统一的,所以夏文化一词很可能指夏氏族或部落的文化。
按徐先生的上述意见,他所理解的“夏文化”有两个指标:从人群上讲,是指“夏氏族或夏部落”;从时间上讲,“所指的是夏代”。他大体是想通过考察“夏墟”内外“文化间的同异”,采取比较的方法找出夏文化。他所确定的“夏墟”主要是两个地区:一个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的上游登封、禹县一带;另一个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大约自霍山以南)一带。从徐先生所考定的“夏墟”范围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要探寻的“夏文化”只是“夏氏族(部落)”的文化,而他所说的“夏氏族(部落)”只是夏后氏,并不包括其他与夏后氏“有交涉的氏族”。因此,徐旭生所说的“夏文化”实际上就是“夏后氏文化”。
徐旭生豫西调查之后,夏文化探索工作又趋于沉寂。直到1977年11月,在“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上,夏文化再次成为考古学界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并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不同观点。为了统一思想,方便开展学术对话,夏鼐先生在作会议总结时首次将考古学意义上的夏文化明确界定为“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不难看出,夏鼐的定义与徐旭生此前所言其实大同小异,都是从族属主体和时间跨度两个方面来界定夏文化的。夏先生的这一意见被学术界广泛接受,成为日后考古学界探索夏文化的出发点,但同时也带来了若干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迫切需要从理论和方法层面来加以解决。
夏鼐所说的“夏民族”应该就是徐旭生先生所说的“夏氏族”或“夏部落”,也就是现在学术界所习称的“夏族”。但这个“夏族”的内涵却是模糊的,因为按徐旭生和夏鼐的定义,“夏族”似乎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并以此与商族、周族等其他族群相区分。但严格来讲,历史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以血缘关系而划分的“夏族”。《史记·夏本纪》称“国号曰夏后,姓姒氏”,足证“夏”是一个地缘性的政治实体,而非一个血缘单纯的氏族。因此,如果单从血缘上论,夏代只有姒姓的各部族勉强可以与这个“夏族”对应,这其中至少包括《史记·夏本纪》所列的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和斟戈氏等多个氏族。而如果非要把“夏”作为族属来理解的话,那么当如相关学者所言,“所谓夏族主要便是各个夏后氏的同姓及姻亲氏族,是他们构成了夏代国家的主体”。这一说法比较接近夏代的史实,但这样一个“夏族”的概念又显然超出了徐旭生和夏鼐的定义。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要强调“夏民族”的内涵,实际上是要明确夏文化探索的主体是什么——这个“夏族”究竟是仅指夏后氏,还是囊括所有姒姓部族,甚或也将那些异姓部族一并纳入?换言之,探索夏文化究竟是探索夏后氏的文化,还是探索姒姓部族的文化,或者是探索夏代所有部族的文化?从过去几十年夏文化探索的具体实践来看,上述三种情况兼而有之,而且都被冠以了“夏文化”的名义,其混乱可见一斑。
邹衡先生是20世纪夏商考古的旗手。在“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上,邹衡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他对夏文化的看法。在随后发表的会议发言摘要中,邹先生明确提出:“从年代、地理、文化特征、文化来源以及社会发展阶段五个方面进行全面考察,可以肯定地说,二里头文化(包括两种类型的早、晚两期共四段)就是夏王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即夏文化。”在这里,邹衡先生明确无误地把“夏文化”定义为“夏王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在此后的相关研究中,他还多次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如他称,“夏朝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夏文化指的又是夏王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又称,“既然夏文化是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首先应该着眼于夏王朝本身,即一个国家,而国家自然有其疆域问题。……把这个范围内已发现的诸考古学文化进行分析,最后便可以确定某种文化可能就是夏文化了”。
正是基于对“夏文化”的上述理解,邹衡先生曾经深入系统地分析夏文化分布范围和夏王朝统治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该项研究中,无论是夏后氏,还是其他姒姓和异姓部族的遗存,只要在时代上大体属于夏纪年范围内,他都一律称之为“夏文化遗存”或“夏文化遗址”。但在这些研究中,邹先生并没有论证为什么这些文化分布区域是在夏王朝的疆域之内——如果当时确实有明确的疆域概念的话。
然而,在其他一些研究中,邹衡先生所说的“夏文化”似乎又回归到“夏后氏文化”这一狭义层面。在夏文化探索的奠基之作——《试论夏文化》一文中,邹衡先生单列“材料和方法”一节,专门讨论探索夏文化的方法问题。邹先生说:
二里头文化究竟是商文化,还是夏文化?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先从分析商文化入手。……只有在考古学上确认了商文化,才能区别出夏文化。……在讨论商文化时,首先要解决的是关于成汤亳都的地望问题。我们认为,只有确定了成汤建国的所在,才有可能进一步探索先商文化、早商文化,从而最后确定何者为夏文化。
在这里,邹先生将夏文化、先商文化和早商文化并举,强调夏、商文化的区分。但是,从年代上讲,夏文化和先商文化在一段时间内是共存的,按照他此前的界定,先商文化就应该是“夏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不应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化解矛盾的唯一方法是,就是把这里的夏文化理解为“夏后氏文化”或商族以外的“夏代遗存”了。
在邹衡先生夏商文化研究体系中,“郑亳说”是一个枢纽。邹先生之所以特别强调成汤亳都在探索夏文化中的意义,实际上就是要确立一个夏商王朝分界线,进而以这个王朝的分界来印证他从考古学文化上所确定的夏商分界线。那么很显然,在此层面上的夏、商文化其实又回归到夏王朝文化和商王朝文化了。所以,在多数情况下,邹先生所说的“夏文化”是一个王朝文化概念,但某些时候,特别是在和商文化做对比研究时,它又常常表现为一个族属文化概念。很显然,这两种意义上的“夏文化”相互穿插转换极易造成困惑,不如徐旭生先生的“夏文化”内涵来得简单明了。
但是,把“夏文化”界定为“夏王朝文化”的做法在学术界颇为流行。夏文化研究领域的另一位重要学者李伯谦先生就曾经指出:
以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得名的二里头文化可以分为二里头和东下冯两个类型,邹衡先生提出的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观点,目前已是学术界基本一致的看法。……二里头类型所属的居民当主要是夏族人,东下冯类型所属的居民当是由少数迁徙至此的夏族人和多数接受了夏文化并受夏王朝控制的当地土著人所构成。
既然把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分别视为以“夏族人”和“土著人”为主体人群所创造的物质文化,那么李伯谦先生所理解的夏文化自然就是夏王朝文化了。
二里头遗址卫星影像
徐旭生、邹衡、李伯谦等学者关于夏文化的不同理解,实际上可以归纳为狭义夏文化和广义夏文化。所谓狭义夏文化,是指以夏后氏为主体创造的文化;而广义上的夏文化,则是指夏王朝各部族文化的总和。因此,当我们说探索夏文化时,首先应该明确是探索哪个层面上的夏文化。
在夏代所有氏族中,夏后氏无疑是最为特殊的一个,它是禹所属的氏族,是姒姓的大宗,或者说是夏王朝的王族,因此该族的文化应该是夏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在夏文化探索过程中,很多学者都是企图通过确定夏代都邑来寻找夏文化的,通过这种方法所确认的夏文化的主体应该就是夏后氏文化。之所以说“主体”是夏后氏文化,这是因为都邑人群构成复杂,文化因素多元。至少从尧舜以降,已经进入部落联盟社会,各部族固然各有居地,但一些部族首领已经集中在盟主居邑(事实上就是最早的都邑)“同朝为臣”,如舜时就有所谓的“四岳、九官、十二牧”等“二十二人”。夏代更是如此,如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羿的身边还有“伯明氏之谗子弟”寒浞以及四贤臣“武罗、伯因、熊髡、尨圉”,这些东夷族人即与夏后氏共同生活在夏都。反之,在后羿代夏之后,夏之遗臣靡也继续留在夏都斟寻辅佐后羿,直到“浞因羿室”之后,靡才“奔有鬲氏”。《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纪》:“初,夏之遗臣曰靡,事羿,羿死,逃于有鬲氏。”凡此种种,足证当时都邑遗址居民构成是十分复杂的。
夏代都邑各部族居民杂处的现象不仅见诸于文献记载,在考古材料上也有体现。林沄先生在研究三代居邑时就发现:
由原来的邑群向国转化的重要之点,恰恰在于国已经是一种地域性社会集团,而不再是一种血缘性社会集团。也就是说,在国这种社会组织中,包含的不再是由同一祖先繁衍的人们构成的诸邑,而是在同一地域中由不同血统的人们构成的诸邑。……二里头文化之混合了多种先期文化的因素,不应单从同一起源的人群对四周人群文化成分的吸收来解释,而应该看成有不同起源的人群在同一地域中错杂居住而造成文化上的交融。如果二里头文化确实是“夏人”的遗存,“夏人”在血统上也是多源的。
毫无疑问,林沄先生这里所说的“夏人”不等于“夏后氏”的族众,而只能理解为“夏都居民”,它所反映的是地缘关系,而非血缘关系。因此,比“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更准确的表述其实应该是“二里头文化是夏都文化”。只是考虑到夏王朝最高统治阶层主要出于夏后氏,所以我们才大体上可以说这类夏都文化的“主体”是夏后氏遗存。
左:2 VM19陶器组合
右:宫殿区墓葬VM11(四晚)
邹衡先生曾经说过,“考古学文化是我们在田野考古中使用的术语,并不是永远使用的名称,如有可能(确有证据),应该尽量用古代的族属来代替它”。李伯谦先生更认为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是反映考古学研究“见物见人”,从而上升到历史学研究高度的重要标志。但毋庸讳言,此类研究鲜见成功案例。究其原因,就在于无论是考古学文化还是古代族群,其内涵都十分复杂,都有很多不确定性,要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难度极大。它既要求研究者对族群的构成进行细究,更需要对考古学遗存进行不同层次的划分。林沄先生在谈到古代族群的复杂性时就指出:“我们通常在讨论这类问题时,所使用‘族’这一词,本来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概念。可以用它来泛指一切见于古代文献的有某种统一专名的人群,只要人群的规模小于原始社会的部落或部落联盟。这种种人群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性质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而严文明先生则将考古学文化分出四个层次,希望“使复原远古时代社会历史面貌、探索氏族—部落分布及其活动,发展的历史的工作成为现实可行的方案,而不仅仅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虽然过去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对考古学文化谱系和文化因素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但远远未到严文明先生所希冀的程度。而且严先生所说的状态,大抵是针对史前社会而言的,当时人群流动相对较少,不同的氏族—部落可能比较集中在某一特定的区域内活动。但对于夏商社会来讲,地缘政治早已取代,至少是相当程度地取代了血缘政治,已经很难区分出单一氏族或部落的活动区域。比如《夏本纪》称有扈、有男、斟寻等夏人同姓是“用国为姓”,它们早已不是血缘单纯的部落,而是人群复杂的封国,要在其中区分出不同部落的文化谈何容易。因此,实事求是地说,在很长的时间内和很多情况下,要通过考古学文化的细分来探索夏王朝时期各氏族(部落)的分布恐怕只是“美好的愿望”而已。这就难怪有学者感慨,在夏文化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甲骨文一类当时的自证性文书资料出土,不可能解决都邑的族属和王朝归属问题”。
而更深层次的思考则来自对考古学文化与族属对应这一研究范式本身的合理性。有研究者指出:
从积极方面而言,这种范式能将海量的出土文物从时空上安排得井然有序,但是其最大的问题在于会将类型学建构的图像与具体的经验事实混为一谈;也即将今天根据器物整理和分辨的分析单位等同于史前人类的社会或生活单位。其危险在于将历史事实大体等同于一种类型学的构建,因为这很容易将用类型学方法排除大量差异而抽取的共性,看作是远古族群和文化的共性。
虽然要在考古学上论证夏代诸族氏的文化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但也不是说考古学对此就毫无作为。一般而言,只有确定了某遗址是某族氏的核心居邑,才有可能比较准确地把握该族所表现出的考古学文化,比如确定了夏代都邑,就能够从主体上了解夏后氏文化。受考古和文献材料的双重限制,目前此类研究还只能做到把某一考古学文化类型与特定的族属联系起来的程度,比如以造律台类型为有虞氏文化,以下七垣文化为先商文化,以辉卫型(辉卫文化)为韦族的文化等。这些研究对于探索夏代文化当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更应该意识到,由于我们对这些族团的构成并不了解,也不掌握它们准确的分布地域,各族氏的核心居邑也未发现,因此上述判断都是粗疏的,甚至有可能是完全错误的,都有进一步深入细化的余地。
鉴于考古学文化族属问题的种种复杂性,我们在进行夏文化探索时应该双管齐下,兼顾广义和狭义的“夏文化”,具体来讲就是:
其一,注重夏代都邑在夏文化探索中的突出地位,把握住都邑文化也就把握住了以夏后氏为代表的狭义夏文化。
其二,注重相关族氏分布区内的核心遗址,通过对这些核心遗址考古学文化的分析来把握各族氏的文化。
其三,将上述相关考古学文化置于相应的历史情境下考察,比较和总结出广义夏文化的基本特征。
二、两种方法:都邑推定法与文化比较法
回望夏文化探索历程,不难发现居于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是“都邑推定法”。此种方法又可粗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将某处遗址推定为夏代某都,典型者如以登封王城岗遗址为禹都阳城,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为桀都斟寻,然后据此推定王城岗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为早期夏文化,二里头文化为夏代晚期文化;另一类则是先论定成汤亳都所在,由此来定早商文化,进而向前追溯夏文化,在夏商文化研究中先后居于统治地位的二里头遗址西亳说和偃师商城西亳说都是循此思路而展开研究的。但在有文字证据之前,企图以成汤亳都来界定早商文化,从而确立夏商分界的做法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无穷的纷争之中,夏商文化的区别只能通过文化的比较来获得;偃师商城西亳说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明显瑕疵,严格上讲,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只是确定了夏商分界的年代下限,因此偃师商城是不准确的界标,更不是夏商分界的唯一界标。
王城岗城址平面图
学者们偏爱“都邑推定法”,固然是因为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更在于潜意识中希望能够找到一处“殷墟”般的“夏墟”,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夏文化问题。这就说明“都邑推定法”是有严苛的前提条件的,它必须寄托于王陵、文字这一类“铁证”的基础之上。试想,如果在殷墟没有发现西北冈王陵,更未发现甲骨文,现在恐怕依然会有很多人怀疑殷墟的性质,晚商的信史地位也就岌岌可危。
表面上看,以都邑遗址中王陵、文字等特殊类遗迹遗物为标准来探寻夏文化是在追求更为坚实可信的科学依据,但殊不知,对于此类证据的刻意追求早已偏离了考古学的轨道——因为考古学从来就不是,也不应该把这类遗迹遗物作为自己的研究主体。换言之,尽管以王陵、文字等“铁证”为主要依据的“都邑推定法”在某些情况下能够有效地解决夏文化问题,但它却不能算作考古学研究——道理很简单,作为一门学科,考古学不可能把自身的研究基础建立在那些可遇而不可求的遗迹遗物之上。换句话说,离开了这些“铁证”,考古学真的就对夏文化束手无策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邹衡先生早就说过,有人之所以“怀疑遗址中常见的陶片能据以断定文化遗迹的年代和文化性质”,那是“因为他们对现代科学的考古工作还不十分了解的缘故”。俞伟超先生其实也有类似的论断,他说:
严格讲来,真正属于考古学自身特有的方法论,主要只有地层学、类型学以及从不会说话的实物资料中观察和分析社会面貌的方法。这里所以把实物资料强调为“不会说话的”,即意味着研究考古发现的文字资料的工作,主要是属于古文字学、古文书学的范畴;至于利用这些文字资料来研究各种古代状况的工作,当然更应是属于其他学科的范畴。
所以,在探索夏文化的过程中,刻意追求文字一类的证据,实际上是对考古学研究方法的不了解和不信任。
“都邑推定法”盛行的后果就是研究者往往容易深陷于某一处遗址或某一个考古学文化,期盼能够从一个点上形成突破口,从而“毕其功于一役”。这种思维方式导致的结果就是大量研究者围绕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大做文章,企图从遗址性质或文化分期上来解决夏文化问题,由此产生了诸多的异说和无谓的纷争。对于这种现象,邹衡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
从50年代末期开始,夏文化的探索者几乎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二里头文化。不过,他们大多数并没有重视徐旭生先生提出来的正确途径和方法,也没有人对二里头文化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直到70年代初期,还都主要从年代上考虑问题。……所有这些论点几乎都没有经过周密的论证,多少都有猜测之嫌,谈不上有什么把握。总之,这些探索只是为数不多的学者用简单的方式各抒己见而已,在学术界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实际上只不过是研究者们“用简单的方式各抒己见”而造成的虚假繁荣。如此严厉、尖锐的批评,应当引起每一位研究者的警惕和反思。
徐旭生先生在夏文化探索领域先驱者的地位,不仅仅因为他是最早调查夏墟的学者,更主要的是,他是第一位摸索出探索夏文化“正确途径和方法”的学者。
徐先生夏文化研究的基石是他对夏代信史地位的笃信。长期以来,他对于极端疑古派“漫无别择”,混淆神话与传说,“对于夏启以前的历史一笔勾销”,“对于夏朝不多几件的历史”解释为东汉人的伪造,从而将“殷墟以前漫长的时代几乎变成白地”的作法极为不满,为此对探索夏文化的方法进行了系统周全的思考。
在1959年开展“夏墟”调查之前,徐先生早已设定了他的研究逻辑:
如果看准当日的中国远非统一,那夏氏族或部落活动的范围就相当地有限制,我们就可以从它活动范围以内去研究夏文化有什么样的相同的或相类的特征,再到离它活动中心较远的地方看看这些地方的文化同前一种有什么样的差异。用文化间的同异来作比较,就渐渐地可以找出来夏氏族或部落的文化的特点。
乍看起来,徐旭生的方法与前述“都邑推定法”并无不同,都是通过对特定区域考古遗存的研究来判断夏文化,但实际上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徐先生研究方法的重点是“文化间的同异”,即将“夏墟”的考古学文化与“较远的地方”的考古学文化进行比较,根据它们之间的差异“比较出”夏文化,因此夏代都邑的有无并不影响他对夏文化的判断。而“都邑推定法”则是径奔都邑而去,直接以夏都文化为夏文化,如果不能论定某遗址为夏代某都,则夏文化也就无从谈起。从表面上看,“都邑推定法”显得干净利落,简洁明快,但如上文所说,它是把自身研究寄托在考古发现的偶然性上的——如果考古学家“手气”不好,没有找到夏都,则一切免谈。而偏偏天不遂人愿,迄今为止也没有确认一处如殷墟一般的夏代都邑,由此“都邑推定法”便生出了无穷的争端,直至开始怀疑夏代的有无。徐旭生先生从“夏墟”而非“夏都”出发来探索夏文化,这一字之差的背后其实蕴含着深刻的学术思考,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徐旭生所秉持的这种研究方法或可称之为“文化比较法”,这种方法想要获得成功,需要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对“夏墟”的正确判断,二是对“夏墟”及其以外区域考古学文化的正确认识。而这两项工作分别是由徐旭生和邹衡先生完成的。
对于“夏墟”的界定,徐先生说:
我们想找出夏氏族或部落所活动的区域,就需要从古代所遗留下来的传说中去找,这就是说在文献所保留的资料中去找。……约略地统计一下:在先秦书中关于夏代并包括有地名的史料大约有八十条左右:除去重复,剩下的约在七十条以内。此外在西汉人书中还保存有三十条左右,可是大多数重述先秦人所说,地名超出先秦人范围的不多。……对我们最有用的仅只不到三十条关于夏后氏都邑的记载,绝大部分在《左传》、《国语》、《古本竹书纪年》里面。……从剩下来不多条的史料比较探索的结果,觉得有两个区域应该特别注意: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地区,尤其是颍水上游的登封、禹县地带;第二是山西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大约自霍山以南)一带。
徐旭生先生的上述认识只是准确地界定了“夏墟”,但在当时,对“夏墟”及其以外地区考古学文化的认识还十分粗浅,这就注定了徐先生不可能有效地完成对上述第二个前提条件的研究,从而在考古学上对夏文化作出具体、准确的判断。归根结底,学者的个人研究一定会受到他所处时代的束缚,即便是徐旭生也莫能例外。
诚所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子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在他所处的时代而论,徐旭生先生能够在传统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利用考古学这种新方法,提出夏墟调查这类新问题,并就调查所获新材料而提出建设性设想,是当之无愧的“预流”。此后邹衡先生审时度势,当仁不让,继徐旭生之后而奋起,也堪称夏文化探索的“预流”。
邹先生自述其夏文化探索的学术背景为:
夏文化研讨之所以进展缓慢,还因为要进行比较全面深入地研究,客观条件仍然不十分成熟,这主要表现在:考古工作的开展还很不平衡,整个60年代考古新发现不多;就是已获得的考古资料还来不及消化,研究仍不够深入。这种情况到70年代才逐渐有所改变。
首先是豫西地区的考古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展。例如郑州商城本来在50年代就已发现,60年代又做了不少工作,但有些关键问题并未彻底解决。经过70年代的继续工作,郑州商城才最后肯定下来。又如偃师二里头遗址中的一号宫殿基址也早已发现,但到70年代才发掘完毕,并提出来二里头文化新的分期。其次,在晋南地区新发现了东下冯遗址和陶寺遗址。再次,就全国范围而言,整个东半部中国的考古工作已全面展开,各种文化的面貌和发展序列已大致清楚。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继续深入进行分期工作外,已有可能开展文化类型的研究了。
襄汾陶寺遗址
基于对考古形势的上述判断,从1977年以后,邹衡先生强烈意识到“讨论夏文化的基本条件已经基本上具备”,“是讨论夏文化的时候了”,并放言“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阅读邹衡先生的相关著述,可以看出他是踵接徐旭生而前行,他的研究也分两步走:先确定“夏墟”的范围,再通过对“夏墟”内外考古学文化的比较来“挤出”夏文化。
邹衡先生《夏文化分布区域内有关夏人传说的地望考》一文就是他为界定“夏墟”范围所作的研究。在这一问题上,他的结论与徐旭生的认识大同而小异,认为夏人的活动区域主要有三处:
一是豫西,可能延及陕东、鄂西,其影响所及,甚至远达川东等地的部分地区。 二是晋西南;其影响所及,或可到晋北,甚至内蒙。三是豫东,可能延及皖西、鄂东部分地区;其影响所及,或可至长江下游。
但上述地域内文化众多,而且按照张光直先生的说法,“在夏代的活动地理范围之内分布,在时代上可以判定为公元前2000前后的考古学上的文化,就有当作夏代文化考虑的资格。”在这些文化中如何抉择,便是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而邹衡先生最主要的贡献正在于他完成了徐旭生先生未竟的事业——对“夏墟”内外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其研究成果就是《试论夏文化》和《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两文。邹先生自己对这两项研究意义的认识是:
《论夏文化》一文对商文化的年代与分期问题算了一个总账,把以往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统统串联起来,并对早商文化重新做了分期。这样,商文化的来龙去脉就基本上清楚了。夏文化的年代与分期问题比商文化要简单一些,该文完全吸取了以往的研究成果,而着重地把夏、商文化各期的对应关系作了比较研究。
……
《论北方邻近文化》一文是与《论夏文化》一文密切相关的,也可说是后者的补充。以往的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多认为商人起源于东方。该文根据大量可靠的考古材料论证了商文化并非起源于海滨,亦非起源于东北。……最后的结论是:历史上夏、商两族的斗争只不过是居于冀州之域的共工族与主要居于豫州之域的夏族斗争的继续。
概言之,邹衡先生通过对上述三个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辨析出豫州之域二里头文化系统与冀州之域先商文化系统在文化面貌上的显著差别,最终得出了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为夏文化的结论,从而第一次在考古学意义上完成了对夏文化的完整论述。至此,一个由徐旭生最早提出,邹衡积二十余年之力才最终完成的夏文化探索的学术体系和研究范式正式确立。当前的夏文化研究依然是在徐旭生和邹衡先生创立的学术范式中进行,未见有突破的迹象。
三、从龙山到二里头:文化比较法的深化
1930年秋,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了山东历城县龙山镇的城子崖遗址,确认了一种以黑陶为典型特征的史前文化——龙山文化。龙山文化一经发现,即与以彩陶为典型特征的仰韶文化共同视为“夷夏东西”的考古学证据。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龙山文化成为黑陶文化的代名词,凡出土黑陶的遗存均被笼统地归入到龙山文化范畴,并出现了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和湖北龙山文化等名称,由此逐渐演变成一个内涵极其庞杂的概念,其中包含有多个具有自身特征、文化传统和分布地域的考古学文化的集合体。鉴于此,严文明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应区分各地区的龙山文化,分别给予适当的名称,同时建议把这些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时代命名为“龙山时代”,这一意见得到学术界广泛的响应。
根据当时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严文明认为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6—前21世纪之间,早于文献记载的夏代纪年,而与古史传说中唐尧虞舜的时代相当。而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龙山时代的年代跨度应在公元前2300—前1800年之间,与夏王朝的纪年有相当部分的重叠。由此可见,无论采取何种测年结果,龙山时代与夏代纪年都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合,早期夏文化必然要在龙山时代的诸考古学文化中加以辨析。
寻找夏文化的空间范围当然要从夏代各族氏的活动区域入手。从夏代都邑分布情况来看,夏后氏最主要的活动范围是豫西的汝颍河上游地区和伊洛地区,但一度扩张到豫东、鲁西和豫北地区。如果一并考虑其他关系密切的同姓和异姓部族的活动范围,则夏王朝的势力范围还可扩张到豫西西部、晋西南、皖北、鲁西地区。
笔者将研究范围扩大到“禹域”内的龙山遗存,同时重点分析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相关特征,以期通过这种长时段、广地域的比较研究,适当地放宽视野,从而找到确立夏文化的关键线索。在对相关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属性进行判断时,均采取统计的方法,首先以翔实的统计数据来辨析出每一处典型遗址的核心器物组合,再以此为主要依据来判断某类遗存的文化属性。应以统一的标准对不同遗址的考古学遗存进行文化属性研究,在此基础上所获结论才具有说服力。在当前条件下,最容易获得的“统一标准”就是每类遗存的核心器物组合,本书对相关遗址的核心器物组合进行了全面梳理,以期正确认识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器物内涵。其中,炊器在文化属性判断上具有决定性意义。这可视作是对“文化比较法”的深化。通过对上表所列的考古学遗存进行历史层面的解读,可以获得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煤山、王湾、造律台、后冈和三里桥等文化类型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共性的文化圈,这个文化圈内数量最多、最具共性的器物是用作炊器的夹砂深腹罐,因此可以称之为罐文化圈。除深腹罐外,用作食器的豆、碗(或覆碗式器盖),用作盛储器的双腹盆和高领瓮(罐)也是具有共性的器类。这个具有强烈共性的文化圈,现在学术界通常称之为河南龙山文化,这无疑是恰当的。从上文的分析来看,河南龙山文化在空间分布上与文献所载夏王朝的核心控制区基本重叠,而且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绝对年代与夏纪年也有相当程度的重合。这种空间和时间上的对应便不宜用偶然性来解释,而只能理解为河南龙山文化,特别是其晚期阶段,应该就是夏王朝的物质遗存。
煤山遗址第一期陶器
第二,上述三个核心区文化面貌的相似性表现出依次递减的态势,即第一核心区内的王湾类型和煤山类型最为接近,主要差别是两个区域内鼎的数量略有参差而已;而第二核心区内的造律台类型和后冈类型与王湾类型、煤山类型之间的差距就更加明显,多甗、多平底盆、多山东龙山文化因素,但在主体上,夹砂罐要占压倒性的多数,罐文化圈的属性依然十分明显;第三核心区的三类遗存其实又可细分为两个层次,其中三里桥类型虽属于河南龙山文化体系,但该类型所表现出的差异性已经非常突出了,远远超过了造律台、后冈类型与王湾、煤山类型之间的差别,多鬲、多单耳罐、多绳纹,夹砂罐甚至很难说是最主要的炊器,罐文化圈的属性已经不明显了。第三核心区内的另一层次是陶寺文化和花家寺类型,从文化面貌上讲,它们都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与河南龙山文化发生过交流和相互影响。其中花家寺类型中的河南龙山文化因素似较陶寺文化更多一些,而陶寺文化对河南龙山文化几乎持排斥态度,倒是陶寺文化的典型器物背壶可以在王湾类型和煤山类型的遗址中可以见到,所以陶寺文化和花家寺类型完全是和罐文化圈并列的其他两个文化共同体。上述三个核心区所形成的四层文化圈与《尚书·禹贡》所描述的甸、侯、绥、要、荒五服实有同工异曲之妙。
第三,从族群的分布来看,上述第一核心区主要是夏后氏及其同姓斟寻、费氏的原居地,此外还包括族姓不明的有洛氏,以及部分“外来人口”如后羿、寒浞等类;第二核心区的族群最为复杂,比较明确的有祝融八姓、有虞氏、皋陶偃姓之后、伯益嬴姓之后以及穷寒氏等泛东方族群;而第三核心区中的皖北地区已知部族有著名的涂山氏,大抵属于淮夷系统,而豫西西部有姒姓的彤城氏,临汾和运城盆地则是陶唐氏的根据地。把族群分布和各区内考古学文化的亲疏远近结合起来考虑,所得结论富有意趣:王湾类型与煤山类型在文化面貌上高度一致,而这一区域内的主体居民是夏后氏、斟寻氏等姒姓部族的族众,同姓部族享有相似的物质文化是非常自然的现象。第二核心区的造律台类型与后冈类型与第一核心区的王湾、煤山类型在文化上的趋同性,则应该是上文所论述的夷夏联盟(也包括祝融八姓之后)的具体反映——一方面,以皋陶、伯益之后为代表的部分东夷族氏已经华夏化,他们在生活方式上与夏后氏等姒姓部族并无不同;另一方面,原产于东方的鸡彝(陶鬶)成为“夏礼”中的核心器类,“夏文化”中蕴含了典型的东方因素。甚至可以说,所谓的“夏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夷夏融合的产物,“血统纯正”的夏文化其实并不存在。而第三核心区诸考古学文化所表现出的独特性,固然从整体上说明这些地区在龙山晚期还不能纳入“夏墟”的范畴,但其中的内涵则各有千秋——在晋南,以陶寺文化为代表的陶唐氏文化在夏王朝建立之后还保持有强大的惯性,依旧占据了临汾和运城盆地的大部,只有垣曲盆地和夏县一带可能是夏文化的分布区;在皖北,由于当地有强大的先行文化——大汶口文化,“历史包袱”过重,尽管有“禹娶于涂山”以及“禹会涂山”这样的历史事件,但作为外来因素的“夏文化”仍不足以彻底改变当地的文化传统,所以形成了花家寺类型这种兼具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土著文化因素的混合遗存;在豫西西部,尽管分布有彤城氏这样的姒姓部族,但这一地区的三里桥类型在文化面貌上与王湾类型和煤山类型差别明显,这恰恰表明考古学文化与族属对应的复杂性,考古学文化完全有可能超越了血缘关系——同姓部族的文化未必相同,而异姓部族的文化未必不同;华夷之辨,最根本的标准是文化,而非血缘。而民族学研究表明,在文化异同和族群之间,很少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能表现族群边界的很可能只是物质文化中的一小部分,而其他特征或式样则为多个群体所共有。河南龙山文化所表现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应该体现了夏王朝多族氏共存的历史事实。
陶寺遗址地貌局部
综合上述解读,我们大体上可以说:在龙山晚期,第一核心区的王湾类型和煤山类型可以理解为狭义的夏文化——即以夏后氏为主体创造的文化。它们又和第二核心区的造律台、后冈类型共同组成了广义的夏文化——即建立在部族联盟基础上的夏王朝文化。而第三核心区的情况则更加复杂,从文化面貌上看,晋南大部和皖北地区虽在不同程度上与王湾类型和煤山类型发生联系,但均不能纳入河南龙山文化体系,都属于独立的文化区;但从政治关系上讲,夏后氏与晋南的陶唐氏以及皖北的涂山氏有着密切关系,陶唐氏(包括其后裔御龙氏)、涂山氏都是夏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们的遗存也可以视为广义夏文化。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撰写《史记·五帝本纪》时就深感困扰,并由衷感叹,“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不足与之言五帝。如今两千多年过去了,不但五帝时代更为渺茫,夏代的信史地位也屡遭冲击。中国考古学本就因重建古史而起,考古学者理应不忘初心,奋发向上,追慕太史公之遗风,为建设真实可靠的信史奉献学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