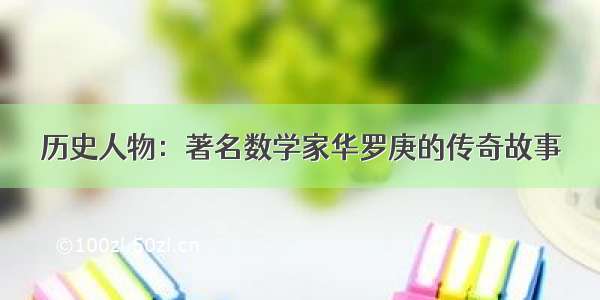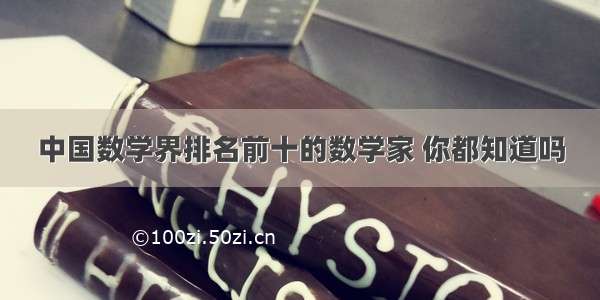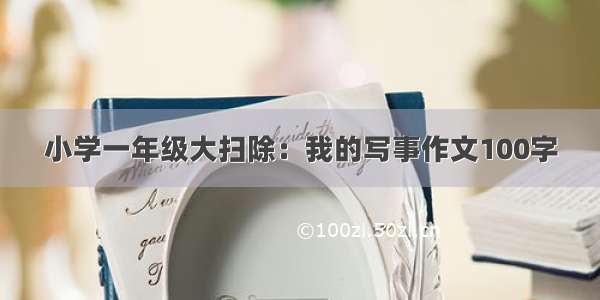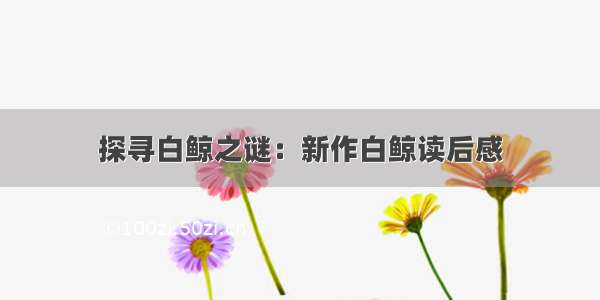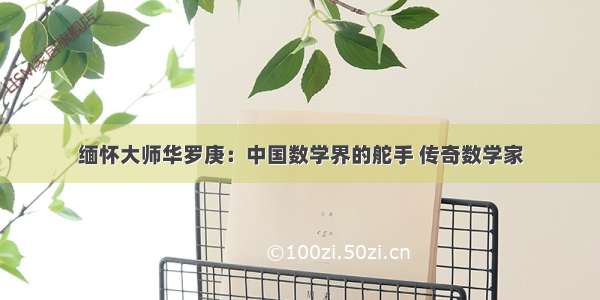
毛泽东与华罗庚亲切握手(1958年)
1978年华罗庚、陈景润、杨乐、张广厚(左起)参加全国科学大会
演讲人:杨乐
演讲人简介
杨乐 著名基础数学家。江苏南通人,1939年11月10日生, 中国科学院院士。1956年起就读于数学力学系,1962年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做() ,1966年毕业留所工作。先后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1998至2002年任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并曾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国数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与数学评议组召集人与成员;中国科学院主席团委员,全国科技奖励委员会委员,《数学学报》主编,《中国科学》A辑主编等职。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院士)。
杨乐在复分析,特别是整函数与亚纯函数的值分布理论方面有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其成果获得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和广泛引用。由于研究成果突出,曾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华罗庚数学奖、陈嘉庚数理科学奖、何梁何利奖与国家图书奖等多项重大奖项。1979年以来,杨乐先后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普渡大学,瑞典皇家科学院,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哈佛大学、圣母大学作访问教授,应邀到美国、英国、苏联、德国、日本、瑞典、芬兰等到国50多所大学和研究所作学术演讲,在20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作主要报告或邀请报告。1996年6月,杨乐与世界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获得者丘成桐教授一起,共同创建了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十余年来中心组织的研究项目与学术活动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
巨星陨落
1985年6月12日晚上十一二点了,电话铃声骤然响起,夜深人静,显得分外响亮。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国内居民家庭安装电话的还不多,我下班回家很少有几个电话,晚上九时以后一般不会再有电话铃响,是看书与思考问题的好时光。拿起听筒,研究所党委书记潘纯同志打来了电话。老潘是位很正派的老干部,然而我们通常只在所内会议上见面与谈话,并没有个人联系。一听到他的声音,我感到可能发生了重大的事情,并有不详的预感。
然而,当我听到他在电话中通报:华老当天下午在日本东京大学作完学术报告以后突发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已于晚上十时逝世时,我还是极端惊愕,茫然不知所措。不仅当时如此,而且在随后的几天里,到机场迎接专机运回华老的骨灰盒,以及到八宝山大礼堂参加告别华老的仪式,我一直为这种惊愕与茫然的情绪所笼罩着。当时,人民日报曾希望我写一篇纪念文章,然而在那些天里,我无法稳定情绪,理好思路,完成这项任务。
不久,我遇到日本数学家H. Komatsu与M.Morimoto教授,他们分别给我详细介绍了华老6月12日下午在东京大学作最后演讲的情况。华老的讲题是“在中国推广数学方法的一些个人体验”,由Komatsu教授主持,四时开始。起初,华老用中文演讲,由翻译译为日语。不久,华老觉得不十分如意,改用英文直接对听众演讲。谈起他自己的研究工作,应用与推广,他感到得心应手,淋漓欢畅。他先将西装外套脱下,又将领带除去。即便如此,据说华老依然汗流不止,以至衬衫有点湿透了。由于内容十分丰富,演讲比规定的一小时超过了10分钟。当演讲完毕,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日本友好人士白鸟富美子女士正要送上鲜花时,华老却从台上的椅子突然滑下。东京大学医院的医生立即实施抢救,但迅即宣告不治,我国驻日使馆仍坚持继续尽一切力量抢救,然而回天乏术,华老于当天晚上10时逝世。
天才在于勤奋 聪明在于积累
早在故乡江苏南通读中学时,便听说过传奇式的数学家华罗庚。当时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张四十年代后期的旧报纸,上面有一长篇文章,介绍华罗庚的经历与故事,把他和陈寅恪并列为两位最具特色的教授。
1956年9月,我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学习。实数、极限、函数连续性等十分严谨的叙述与相关的理论,让许多同学遇到障碍,感到困难。然而,他们在中学时都是数学成绩突出的优秀学生,于是一些人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学习数学,专业思想产生了动摇。这时,系里请来了华罗庚教授给大家做报告。报告在北京大学的办公楼礼堂举行,作为一名听众,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伟大的学者。在报告里,华老提出要随时发现问题,并努力思考。他举例说,在街上看见一辆汽车牌照的数字,那么就可以问它是不是素数,或者它正好是几个素数的平方和或立方和,这使大家感到十分新鲜与有趣。华老特别指出,天才在于勤奋,聪明在于积累。一些悲观的同学受到鼓舞,重新树立了努力学习的信心。
1959年,我们上四年级时分了“专门化”,我所在的“函数论专门化”有二十余人。当时还组织活动,到中科院数学所请华罗庚先生给我们讲学习函数论的意义与方法。在华老的办公室里,我们围坐在他身旁,聆听他的教诲,感到十分亲切,受到很大的鼓舞。
真正与华老有稍多一些的接触是在1962年我由北大毕业,考入数学所成为熊庆来先生的研究生以后。当时华先生是所长,熊先生则是函数论研究室的主任。华先生在多复变函数论的研究生钟家庆、孙继广、曾宪立,以及熊先生的研究生张广厚与我,都在函数论室,平时与已经工作的青年科研人员没有什么差别。钟、孙、张与我在北大六年均是同一小班的同学,十分熟悉;曾宪立在北大后三年,也与我们四人在同一专门化,相互了解。
当时,熊先生已年逾古稀,半身不遂,极少来所。华先生刚五十岁出头,经常到所上班,他的办公室位于四楼正中(412室)。他约其研究生谈学习与研究工作时,有时也把张广厚与我一起找去。头两次主要是谈打基础的重要性,华老特别要我们认真研读E.C. Titchmarsh的函数论。谈话最后,他谦虚地对我们说:你们是熊先生的研究生,我的话作为参考,你们要听从熊先生的安排。
拳不离手 曲不离口
五十年代末,随着大跃进的浪潮,数学所规模扩大了很多,几年间进了不少人。1961年至1962年,全国进行调整,华老作为数学所所长,觉得要在所里认真开展研究工作,就必须对那几年到所的年轻人的业务摸清底细,以便打好基础。1962年上半年,对全所青年科研人员进行了考试,内容并不高深,只是华老一向重视的基础:“三高”,即:高等分析、高等代数与高等几何。然而有些年轻人成绩很不理想,甚至是零分。
针对这种情况,华老在全所大力提倡打好基础,提出“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办起了提出数学问题和征求解答的壁报,就放在他办公室外的墙壁上,称为“练拳园地”。
关于研读经典著作与文献,打好基础,华老有不少名言与精湛的方法。例如,他提出:读书要先从薄到厚,再从厚到薄。其意思是,数学书一般写得比较精炼,省略了一些推导与计算步骤,开始学的时候必须十分认真与仔细,将这些省略的计算与推导补齐,这就是从薄到厚。等到这本书学完以后,不可能全部细节留在脑子里,而是将最重要的思想和提纲保留着,这样就由厚到薄了。
在全所青年人员考试以后,华老还对在科研工作上有显著表现和成绩优秀的人员作了提升。王元、陆启铿、万哲先、丁夏畦、王光寅等提升为副研究员,陈景润、许以超、岳景中等成为助理研究员。与此同时,又将成绩很差的人设法调动工作,离开数学所。这种“考试、提升、调动”的做法后来受到了非议,加上有人认为纯数学研究理论脱离实际,使得华老于1963年底毅然离开了数学所。经反复协商、挽留,华老仅同意保留所长的名义,而研究工作与培养学生则改在中国科技大学进行。
虽然如此,在几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华老还是未能免去遭受数学所造反派冲击的命运。他过去的做法被称为是砍向革命群众的“考、提、调”三板斧,大受批判。华老作为反动学阀,被造反派严厉批斗。批斗会上,“打倒华罗庚”的口号彼伏此起。会后还让素有腿疾、行动不便的华老打扫走廊卫生。当然,与苏步青教授等在学校里受到年轻学生更多的凌辱与体罚相比,华老的处境已经算是较好的了。
提携青年
1976年10月,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华老重新焕发了青春活力。我也有很多机会与华老接触。1977年初,我和张广厚的科研工作得到新华社与全国各大报纸报导后,一次华老向我和张广厚说起:“当时,我在黑龙江推广优选法,因病住进哈尔滨的医院,医生和护士问我,报上刊载的杨乐和张广厚是不是你的学生?我说不是,他们两人是我的师弟,我们有相同的老师熊庆来。”无独有偶,1988年9月陈省身先生请我在南开数学所作学术演讲,由他亲自主持并作介绍,介绍中也特别提到“杨乐教授是我的师弟”。能为华老和陈先生这两位伟大的数学家认作师弟,这是我无比的荣誉。
华老对他的学生与其他青年人,也是满怀期望,全力培育与帮助的。六十年代初刚到数学所时,就听说华老在讨论班上要求如何严格,学生在黑板前讲解、推导与演算时,华老不断提问,并且穷追不舍,以至一些学生最终难以回答,这种情况称作“挂黑板”。我到所后,已经很少看到这种现象,较多的则是华老对大家的期望与鼓励。例如,华老当时说:我希望年轻人站在我的肩膀上,向上攀登。
华老勉励青年人,提出学习要十分勤奋。他说:年轻的时候,别人用一个钟头做的事情,我用两个钟头来做,并且将这种做法长期坚持下去。过了几年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别人需要一个钟头做的事情,我二十分钟就做完了。三十年代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书的钱伟长教授,曾向王元和我说起,他原想习文,“九 一八”事变使他改变了志愿而学习物理,但他并未受过中学的系统教育,于是在清华时十分用功,每天早上五点钟就起来念书。原来以为自己是全校最用功的,后来才发现华罗庚先生比他还用功,每天早上四点半钟就起来念书了。
华老提醒青年人要学习前人已有的知识,注意积累。他说在清华刚开始学复变函数论,他就证明了一些定理,起初以为是新结果,后来才知道这些是Cauchy定理等等,是早已有的。他还说,如果没有后来到清华与剑桥大学获得很好的学习与做研究的机遇与环境,如果他仍然留在金坛老家,充其量只能做一位较好的中学老师。那时在金坛,华老能看到的最深奥的数学书就是一本50页的微积分。
华老还对我们说,当学生和年轻人提出问题时,应该当时和他们一起做,而不是回去经过认真与精心的准备,第二天将漂亮与完整的答案拿给他们。和他们一起做,就会使同学们看到,无论是老师或者专家,并不是拿到问题后就有完整的想法,也可能茫然,可能碰壁,或者走入歧途。在推导与演算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可能遇到困难与挫折。经过一番努力,最终才将问题解决。这样可使青年同学知道专家和老师并不是天才,他们自己也不愚蠢,从而增强学好数学的信心。
1979年3月,中国数学会在杭州举行全国理事会议,浙江省与杭州市邀请部分数学家与青少年见面。在杭州一座很大的剧场里坐满了大约两千余位中学生,华老、苏步青、江泽涵、柯召、吴大任等老一辈数学家出席了见面会,我也参加了会见。华老讲话勉励同学们努力学习,长大成才。见面会前一阶段结束后,华老等退场,由我向同学们作关于学习数学的重要意义与学习方法的报告。我还记得华老退场时,微笑着向我说:“这里就交给你了。”我顿时感到肩上的担子重了起来。
汇报演出 弄斧班门
学术交流对数学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华老对此十分重视,并提出要和同行专家、和高手进行交流。他常说,弄斧必到班门。
1981年初,华老访美五个月返国。他提出:演员们出国或到外地巡回演出,回来后要作一次汇报演出。现在,我们许多学者都出国作过访问,在外面作过什么学术报告,学到了什么,我们是不是也来一次汇报演出?于是,他以身作则,到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作学术演讲,为时四周。王元、谷超豪、夏道行、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