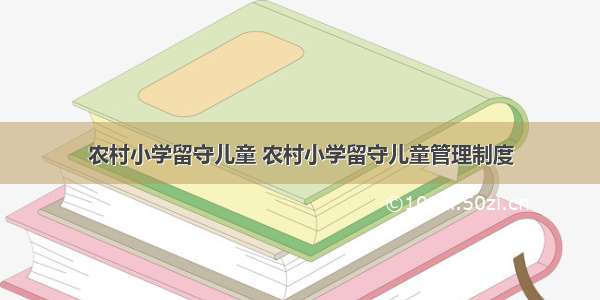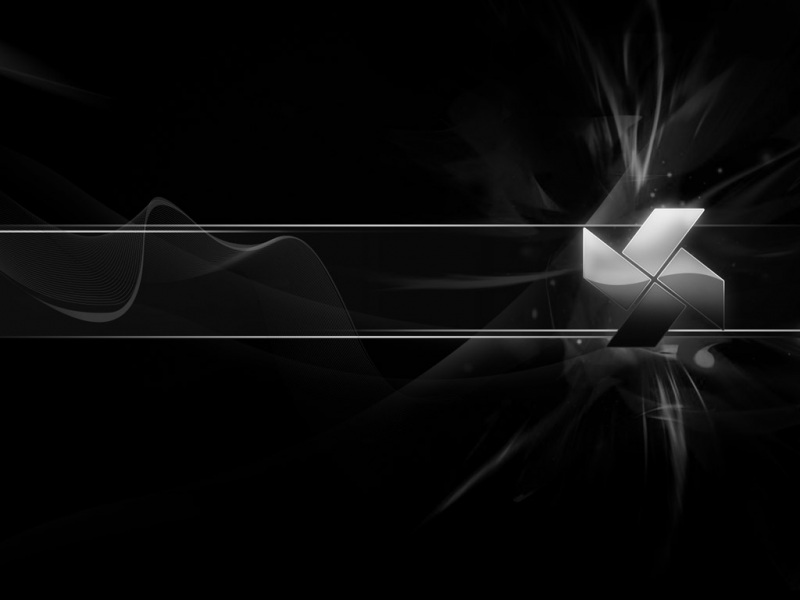留守儿童的生活状况和情感饥渴段成荣的分析表明,在留守儿童中,因父母一方外出而与单亲一起生活的占43.8%,其中与父亲生活的占10.5%;因双亲外出而与(外)祖父母或其他亲属一起生活的为51.7%,独自生活者占4.4%.中央教科所的五县调查资料显示,与父母一方生活者为56.4%(其中与父亲生活者为3%),与祖辈一道生活者32.2%,与其他亲友一道生活者5.0%.总起来看,那些单亲外出的孩子绝大多数与其母亲一道生活。在这些家庭中,“父母”这一共同角色组合改由母亲一人承担,孩子们实际上长期生活在父亲缺位的单亲家庭中。尽管目前的研究还难以描述传统“严父”角色的大面积缺位和相应教育职责的丧失可能造成的具体影响,但可以肯定那是一种不健康的影响。至于那些双亲外出的少年儿童(依照段的结论推算,在2000年全国农村已有1000万人),通常有80%左右被托付给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组成“隔代家庭”,少部分寄养在其他亲友家中,也有的是独自生活,成为父母健在的“孤儿”。在广西南宁的13万多“空巢学生”中,“没有临时监护人”的竟然不可思议地达到73659名,占55%.经验表明,由于受托人的能力和意愿等因素,托付给祖辈或其他亲友的留守孩子所受到的关爱和监护一般会逊色于其父母。正如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会长(曾经是中国意识形态的领导人之一)徐惟诚所言,“爷爷奶奶除了代沟的差别大之外,还有一个天生的难处,他不好多管,讲重了不对,讲轻了也不对。讲重了,他怕儿媳妇回来对他有意见,所以他宁肯少讲。”进一步的问题在于,远距离流动导致的交通不便、经济成本的考虑以及其他难以确定的原因,导致留守儿童与其父母见面的频率一般都很低。中央教科所的五县调查显示,只有那些在本县务工的父母才有可能每月回家看望子女,而流到外省的往往一年甚至数年才能回家一次。在四川眉山调查的近6000名留守学生中,父母一年回家一次的占50.7%,二年回家一次的占17.5%,三年以上未回家的占12.7%.问题还表现在天隔一方的亲子之间联系稀缺。根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课题组8月对安徽、河南、湖北、四川等中西部10个省区115个自然村的留守儿童状况调查,“大多数父母与留守子女的电话联系频率不足1次/月”。在接受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访问的父母中,60%半个月或一个月与孩子联系一次,10%平时很少联系,只在过年过节时回家看看。在广西区妇联抽查的南宁农村600名“空巢学生”中,平时在生活上能得到父亲和母亲照顾的分别只有11.5%和11.7%;28.9%的孩子经常与父母联系,而“有时”和“很少”联系的分别占39.4%和25.9%.另有23.7%的孩子不知道父母在何处打工,没联系过、联系不上的分别为3.3%和2.2%.3,作为社会问题的“留守综合症”父母的关爱是少年儿童乃至人的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财富”,而关爱的缺失必然导致严重的情感饥渴和生存障碍。来自四川的两份报告写道:“有的孩子每天将父母的照片放在书包或衣袋里,有的人流着泪在日记中多次呼唤:”爸爸、妈妈,我想你们,你们快回来吧!你们不要我了吗?‘“”某乡中心校三年级一班有个学生,家里有2姐妹,姐姐12岁、妹妹9岁,由于父母均外出打工,没人管,经常没饭吃,上课时饿晕了……“在缺少父母关爱和监护的情况下,他们更多地暴露在逐渐恶化的社会环境中,使得原本薄弱的学校教育因为家庭教育的缺失而大打折扣,从而造成社会化过程的严重扭曲。表2收录的资料表明,这个群体存在着较普遍的心理和性格方面的障碍,学业更容易受阻,行为也更容易越轨。
在这种可以称为“留守综合症”现象的背后,我们从近两年的新闻报道中时常可以看到留守孩子因无法摆脱压抑和孤独而选择“自杀”的消息,也可以看到足以称为“人道主义灾难”的极端案例。而一连串的事件表明,留守儿童群体实际上遭遇着较为严重的生存危机。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孩子对父母常年在外表示“恨他们,自己被遗弃了”。四川眉山农村一位11岁女孩,因长期在外的父母杳无音讯,当调查者问及有关父母的问题时,整整半小时,常年沉默寡言的她痛哭不已,只断续说了两句:“我不想父母……我不希望他们回家。”重庆东部某区一名15岁的初中生,很聪明,原来成绩很好,父母外出打工,后来又离婚,长期随爷爷奶奶生活,他经常旷课、看录像,成绩严重下滑,甚至产生了厌世情绪,认为自己是多余的人,在一篇作文中追问:“来父母给了我什么”。而当认识到父母的外出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成为一种被迫的行为之后,不满乃至仇恨的对象也就发生了转移,“一些留守孩子认为社会对他们不公平,产生仇视他人、仇视社会的倾向。”“恨社会不公平,父母没办法才出去”。
无须强调这种危险情绪的社会后果,它在不确定的时间内极有可能转化成实际行为。客观而言,无论是有意识的仇视还是不自觉的误入歧途,广泛的留守状态确实成了适宜繁殖“问题少年”和“不良少女”们的丰厚土壤,从而既使中国近年来的犯罪浪潮愈加凶猛,也为今后的犯罪提供了庞大的预备军。对两项分别来自法院系统和公安系统的数据进行简单对接,可以确信上述判断确实不是耸人听闻:——2000-,全国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以14.18%的幅度逐年上升,而截至7月,未成年犯罪案件又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3.96%.(《北京晚报》9月16日)——公安部的调查显示两个“大多数”:全国未成年人受侵害及自身犯罪的案例大多数在农村,其中大多数又是留守儿童。(《解放日报》8月31日)
三,家庭的“空巢化”与独居老人在不考虑农民流动因素的情况下,中国农村的“老人问题”原本已经相当沉重。这主要是基于如下两个背景。第一,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人口平均寿命的增加,农村的“老龄化”进展迅速,按照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衡量,农村的老龄化率2000年已经超过城镇,当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为7.35%,而城镇为6.30%.其中浙江、江苏、山东、北京和重庆农村分别达到了10.51%、9.73%、9.15%、8.35%和8.04%.在未来较长的时期内,农村老人的绝对数量会继续增加。第二,应该受到公共财政大力支撑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远没有建立起来,只能依靠子女养老的他们又遭遇年轻一代“孝道”观念弱化的冲击。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在农村老人中,只有2.8%的人(在城市为65%)拥有“退休金”作为生活来源,靠子女供养者占86.1%.而大量的经验资料表明,子女们已经难以再成为令人无忧的依靠,农村赡养纠纷的增加,以及关于农村老人自杀率为世界之最的研究结论,都说明农村老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中最为弱势的群体。在这种背景下,这个群体又要面对子女离乡的新问题。从宏观上说,青壮年农民的大规模流出提高了农村常住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增加了无法与子女共居的“空巢老人”或老年空巢家庭的数量。200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表明,中国农村60岁及以上老人中与配偶一道生活的占25.3%,单独生活的占7.6%,两者合计占到了老年人数的三分之一。而随着此后农村青壮人口的进一步流出,这种比例无疑进一步提升了。让我们利用一些地区性的调查或普查结果来观照这方面的状况。据对北京市人口统计数据的分析,2002年全市有老人空巢家庭45万户,占有老人家庭的37%,其中农村的老人家庭空巢率为38%,超过了城市的36%.天津市宝坻区夏天对22个乡镇的调查显示,单身独居老人和只有两个老人留守的家庭占到被调查总数的45%.7月14日《重庆晨报》的报道说,在重庆市的400多万60岁以上老人中,空巢老人达181万,占全市老年人口的43.7%,其中单身空巢老人31万左右。而农村老人空巢化的状况也明显高于城市:三峡库区15个县区为48.3%,渝西经济走廊地区11个县区44.5%,渝东和渝西少数民族地区5个县区为38.8%,均超过主城9区33.5%的平均数。上述几项调查统计是以整个县级区域为单位的,包括了县城和镇的状况。我们利用一些对于村级单位的个案调查资料,来进一步考察“纯农村”的状况。据吴业苗夏天对安徽省庐江县西村、胜利村,无为县河东村和含山县王庄村等4个行政村家庭情况的调查,当地空巢家庭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分别达37.2%、36.6%、41.1%和49.6%,而其中“老年型”空巢家庭分别为13.4%、14.3%、14.1%和19.8%,四村平均为16.1%.
吴的调查结果显示了那些子女不在身边的“严格意义上的”老年空巢家庭占总家庭户的比例。由于其分类不包括“未生养子女家庭和光棍家庭”(自然也排除了五保户),因此结论中的“老年型”空巢家庭达到16.1%的情况,可以看作主要是由于子女外出造成的——虽然作者本人没有提到四村劳动力外出的情况。进而,如果将作者排除掉的部分重新纳入统计,独居老人的比例无疑会进一步增加。不过,这种遗憾有两项调查可以弥补。较早于1999年对重庆79个村的调查显示,在14332名老人(不包括无子女的“五保户”)中,与子女分居的老人家庭高达有老人家庭的56.7%.而安徽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初对肥西县马店村的调查则呈现了包括“五保户”在内的农村老人的整体状况:在这个拥有2237人()的村庄,60岁以上的老人231人,占10.3%,其中独居及夫妻共居者164人,占全村老人的71%.如果说注重经验的传统农业文明的衰落意味着老人地位的下降有一定的必然性,那么,青壮年的大量流出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个庞大群体的弱势。固然,从积极的意义上讲,青壮年的外出务工将有助于提高其经济上赡养老人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是否确实会转化为现实的供养水平,还留有疑问。安徽省农调队对马店村的调查表明,农村老人仍然处于普遍的贫困之中。,该村231位老人的人均纯收入仅720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775元,分别只相当于马店村全体村民人均纯收入(2650元)的27.2%和人均消费支出的34.7%,只能维持最基本的温饱;在居住方面,虽然钢混结构及砖木结构住房面积已占当地全部住房面积的90%,但老人们住的“往往都是家中的老房,有的甚至是危房。”因此,青壮年外出带来的更多是雪上加霜。第一,由于缺少来自于子代的照料和交流,使得老年人群的孤独感更加普遍和深刻,从而在体弱多病的时期特别容易遭受心理健康危机。天津市宝坻区的调查发现,在这个“常年患病的比率高达70%以上”的人群中,“生活自理的占65%,半自理的达到25%,完全不能自理的达10%”,他们大多过着“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的寂寥生活。在肥西县的马店村,“多数老人天一黑就上床睡觉”。许多人由此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甚至觉得余生便是“带着病痛等待死亡”。由于无人照应,遇到身体不适,只能是大病小看,小病不看,死在家中多日后才被人发现的事件时有发生。
第二,它使得那些本该退养的老人被迫继续承担繁重的劳动。前述肥西县马店村的调查显示,青壮劳力外出后“农活大多交给了老人。老人们起早贪黑地操劳,农忙季节往往不得不进行超体能的劳动。”该村60岁以上老人中常年参加劳动的119人,占老年人口的一半以上。在儿子媳妇双双外出的情况下,他们要承担起抚育第三代的重任,这明显超出了他们的负担能力。而对于那些男人外出而媳妇留在家中的家庭来说,老人虽然只是农活、家务和照看孩子上的帮手,但却往往成为“吃力不讨好”的帮手,那位因丈夫常年在外而同样面临心理困惑和实际困难的媳妇,往往容易同公婆之间滋生矛盾,又因为缺少儿子在中间的缓冲与沟通,很可能就产生不可收拾的结局。初来自南京市六合区的一篇报道,显示了并不起眼的日常性事件对于乡村家庭和老人的巨大冲击:
南京江北某医院急诊室负责人透露,仅去年,该院就收治了上百例因婆媳矛盾引起的喝农药、上吊自杀者,其中婆婆占多数。据介绍,自杀者大多来自乡村,矛盾焦点集中在家庭琐事上。由于近年来农村主要劳动力、家庭男子纷纷外出打工,剩下婆媳和小孩在家,常常在赡养费、带小孩、送孩子上学、做家务、烧煮饭等方面发生分歧,稍有不到位,便言语不合,矛盾升级。由于儿子长期在外打工,老人怨气和委屈无处讲,媳妇有时只得忍气吞声,双方互不沟通,埋怨和误会越积越深,到一定程度后,便失去理智,选择自杀。六合区某村七旬老妪黄某,40岁时丈夫因病去世,她含辛茹苦把三个儿子抚养成人,均已成家立业。然而,老人并没有因此过上好日子。近几年,三个儿子分别外出打工挣钱,三个儿媳视老太为累赘,不顾老人体弱多病,强要老太为各自家庭洗衣烧饭带小孩、养牛。老太整天奔忙于三个儿子家,自己一天三顿就用罐子在柴锅灶里炖。如果做事不顺儿媳心,就会遭到破口大骂。一个月前,婆婆因在外放牛受凉感冒发高烧,不能起床,二媳妇张某不分青红皂白,把老太从床上拽下地要求干活。村里人认为,多年来被三个儿媳虐待的老太是看在外出打工的儿子和可爱的孙子孙女身上,才勉强活了下来。而就在当天,老太被儿媳拽到地下后,突然感到心灰意冷,绝望之下在自己破屋内上吊身亡,结束了痛苦的一生……——《现代快报》1月6日讨论:从家庭的解体看中国农村的重建在分析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台湾乡村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人口急速外移而导致农村劳动力不足和只有老人孩子居住的破败现象时,一位台湾的人类学家曾经论道:“实际上它可能已在形成另一种不同的社会形态,而不再是有关农村兴衰的问题”。这一稍显匆忙的结论应该说体现了人类学家的高屋建瓴,但是,新的“社会形态”或“两地社会”之类的概括并不能替代对其实体的具体分析。我们有必要追问:这种社会对于其中的人意味着什么?它是否适宜于人类——无论是台湾的“农民”还是中国大陆的农民——的居住和生活?从表面上看,农村的衰落、解体乃至终结,在西方和东方的工业国成为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而且被一部分学者看作是文明演进的自然结果或“普遍规律”,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本身似乎就意味着对农业和农村的取代和否定。但是,稍加考察可以看出,与西欧和美日等国家在不同年代出现的农村人口/劳动力的外流及其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57)相比,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的状况都更加独特:一面是外出者无根飘零,遭遇着“黑心老板”的压榨、城管队员的驱赶以及“小市民”们的白眼,一面是“留守者”们同样的紧张、孤独、痛楚和无助。正如“后院起火”这一中国式的成语所包含的意蕴那样,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流动引发了如此迅猛、广泛和深刻的家庭解体,乃至于形成名副其实的人道主义危机。因此,在文明演进的结果或“普遍规律”之前,必须加上“中国式的”这一限定用语。也就是说,主要是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农村家庭如此迅速的断裂和人的碎片化,从而也就颠覆了农村社会的根基。可以推想,如果它的城乡差距并不是世界第一而只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如果它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能够稍微健全一些,如果它的农村义务教育制度不主要表现为农民的“义务”,那么,可能就会有相当多的已婚男女不必迫于生存的压力而同年轻的姑娘小子一道焦急地奔向城市。进而,如果城市能够表现出多一些的宽容,不只是施舍般地接纳一个拥有“暂住证”的“劳动力”,而是同时容得下一个完整的家庭,那么,中国式的离婚、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的规模就不会如此之大,农村家庭和社会的解体也就不会如此迅猛。
不过,仅仅指出这一点可能并不完整和中允。实际上,那些直到现在也并没有完全消失的反对农民进城或“彻底进城”的理由,虽然确有无视农民权益的城市中心主义偏向,但并非没有现实的论据支撑。在中国城市经过二十年的扩张,大城市膨胀成“特大城市”、特大城市膨胀成已经看不到完整躯体的超级巨无霸的今天,从选择符合人性的居住空间的角度来看,那些最有吸引力的特大城市可能确实无法再容纳大量的人口。这就涉及到中国的城市化战略以及整个国家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问题。撇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类带有虚幻色彩的政治动员性口号,回到乡土中国重建的实在问题,在小规模的农业经营已经不足以维持新的社会状况下农民的生存经济,而必须通过“打工”来弥补的今天,如果说确实只有通过城市化和工业化才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那么,有必要重新温习和进一步研究费孝通先生当年提出的“离土不离乡”命题。是否如政府官员、开发商和学者们组成的大城市崇拜共同体那样出于政绩、形象和利益而极力“将城市做大做强”,从而导致大量农村人口的跨省区流动(一种远距离、高成本的“异地工业化”和“异地城市化”),还是站在家庭、生活、人性的角度,通过宏观而又具体和系统的政策引导来推进农村人口的就地就近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