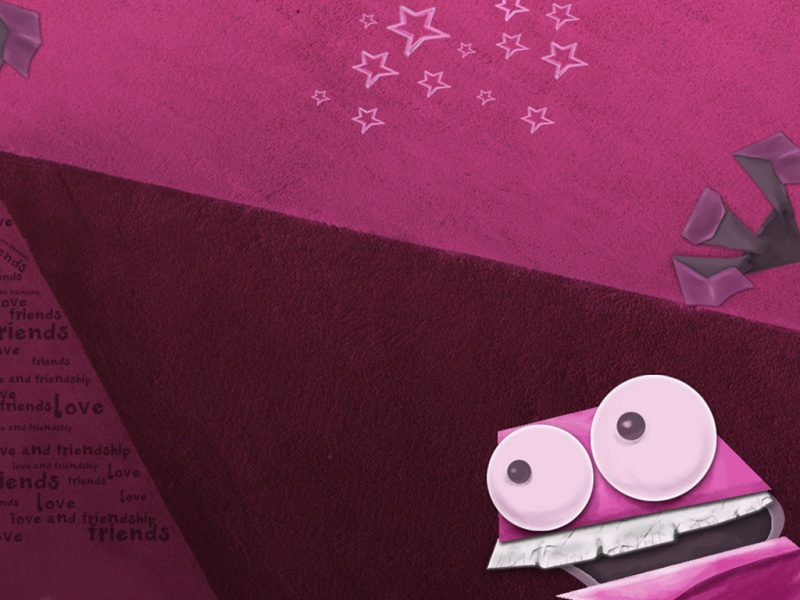1
长宁侯府的老夫人病了。那个向来走路挟风带电,说话中气十足的老夫人似乎是被气病的。
丫鬟们说,前日晌午那个身穿白夏布对襟衫子,乌发蓬蓬的小娘子,来府上和老夫人说了几句话,不知怎的,老夫人就被手中的茶呛了一口,头便发了晕,脚也发了软,手抖着指向那个娉娉婷婷的小娘子:
“这是什么世道…….简直世风日下,不成体统,不成体统……”
丫鬟们还说,那是个顶好看的小娘子,大概有十个长福郡主那般好看。长福郡主的样貌是京城里拔尖的美人,有十个长福郡主那样好看,那不就是仙人?丫鬟们说仙人好看得让人挪不开眼睛,几双眼睛净顾着看仙人了,没太仔细听老夫人她们说了什么。好像是,大概是:
“小娘子何人?”
“祁洲,齐氏,单名瑟。”
“小娘子何事?”老夫人又问。
“求嫁。”
“嫁谁?”老夫人手一抖,心一慌。
“长宁侯,朱彻。”
落后,那小娘子又走到老夫人身边,凑过去说了些什么,老夫人就倒抽冷气,一口茶噎在嘴里呛的满面通红,然后就病了。
全京城的人都知道,长福郡主和长宁侯幼年时就被当今圣上结了亲!
看着主位上的长宁侯置若罔闻,满屋子丫鬟私下咬着耳朵。
“你听过祁洲吗?”侯府的绿衣丫鬟皱眉问。
身边年长的圆脸婆子道:“我只晓的府路县,哪听过什么洲。不定是那个犄角旮旯里来的。”
圆脸婆子摆摆手,一脸茫然。
对话进了其他丫鬟们耳朵,都拿眼瞅瞅朱彻,满心的义愤填膺。
这到底是哪里来的乡野女子,仗着好看的皮囊——这么不知廉耻的来鸠占鹊巢,棒打鸳鸯 。
主位上的朱彻,正斜倚在黑漆交椅上,一身朱红广袖大袍鹤氅被他穿得又正经又骚气——老夫人说了,穿红的能祛灾辟邪,他就春夏秋冬里不带重样的红。一张脸面冠如玉——老夫人又说,外头怕着了风,淋了雨. 他就长年待在宅子里沤得脸白腻腻的颜色。一双眼浓黑如墨,深不见底;一双唇却是没有人气的苍白寡淡。
长宁侯府的老侯爷早些年就去世了,只得朱彻这一嫡子,便由他承袭了爵位。年近四十才得这个儿子,老夫人把朱彻看得如珠如宝,心头肉一般。奈何这心头肉,自幼时,就三天两头的病;这些年宫里的太医一个个轮着快把长宁侯府的门槛踏破了;长宁侯府的老夫人又快把寺庙佛堂的门槛踏破了。
真是可惜了,这么个眉目如画,形貌韶秀的好郎君,丫鬟们暗想。她们都知道长宁侯朱彻的病是病到皮肉里,病到骨子里。
已经有仆妇小斯开始用大红绸子把长宁侯府挂的红恍恍的,院子里但凡开得白色花都给掐掉换上红色的绢花,到处张灯结彩,一派喜气临门。
“再然后呢?”朱彻明知故问。一只修长无节的手,一下又一下的敲着檀木镂花云纹几案,似乎在就着音律打拍子,闲逸得跟没事人一样。
“再然后,然后老夫人就答应了,还许了她泼天富贵,万两银钱。”丫鬟们说。
小娘子走后的第二日,长宁侯府的老夫人,便拖着病身子,往皇帝面前插烛似的一跪,从老侯爷保家卫国战死沙场讲到如今孤儿寡母撑起门户,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就舍了名满京城的长福郡主,定了边鄙之地,青州府来的齐瑟。
盛京城内的百姓都在传:大概这齐小娘子怕是祖坟冒青烟,还是那种冒得浓浓的青烟。不然怎么能讨得侯老夫人的青眼,青云直上,飞上枝头。
2.
“小娘子,现在我们是江陵府人,不是祁洲。”丫头子秋豆看着齐瑟,一脸认真的纠正那日齐瑟的自报家门。
“哦,我忘了改朝换代都几茬了,祁洲不叫祁洲了,成了江陵府。”齐瑟说。
齐瑟的宅子在盛京城南安门往东。在街角一隅,偏僻寂静,鲜有人来,这座宅子什么时候有的,没人记得。仿佛一直不存在,又一直存在,人事琐碎,谁会记得那么清?
那日长宁侯朱彻来的时候,是带着排场来的。那会儿齐瑟正坐在穿廊下的一张凉椅上,拿轻纱团扇摇凉儿。
丫头秋豆提着裙角风风火火,满头细汗的跑了进来——小娘子说了做人得有做人的样子,不似在祁州的洞府中能飞檐走壁,自在跳脱了。
“小娘子,前几日咱们去的那府上,今日来人了!“
“嗯。来人便对了。”齐瑟手中的轻纱团扇停了下来,眼神瑰丽莫明。
“莫不是那天他们一生气,来家上房揭瓦的?”秋豆眉眼一皱,担忧道。那些个人可真讨厌,她们当狐的时候,人撅她们的洞,她们当人的时侯,他们又来拆宅子。往哪哪不安生。
齐瑟摇摇头,迎了出去。
秋豆愣在后边,不是来拆宅子,那是来干什么?
齐家大门大打开,秋豆掩在朱漆金环的门后细意观看:一个八人抬的大轿子在门首并未落轿,有仆从掀了帘幔,恭身侍立的在一旁打着扇子。朱彻身穿了朱红大袍,眉目朗朗,面冠如玉的就这么端坐在里头,名贵的似一朵盛世牡丹。
一身白绫对襟衫子,豆青罗裙的齐瑟立在朱红的门首。潋滟的双眼,琼鼻檀口——人间哪养的出这样的颜色!
得是千年修行,积德布善得来造化!她们狐族本就容色天成,日久年湮的修行,又沾了仙气。
“去府上求嫁的便是你?”朱彻面色发冷。
“是。”齐瑟浅笑嫣然的看着他,答得利落干脆。
丫鬟秋豆脚一软,险些栽倒:小娘子好好的洞府不待,要跑来嫁人?而这个人是红尘俗世里,将死之人。有什么意思?秋豆不懂。
“你图什么?”朱彻似乎来了兴致。
“都说长宁侯眉目如画,一世无双。我当然是图你的人啊!”齐瑟说。
“当真?”朱彻眉毛一挑:“看不出齐家小娘子是个好色之人。”
“还是个好财之人。”齐瑟指着轿子后面,替他补充。是啊,她得图点什么,他才会信她。俗世之人都爱钱财,他大概就会信了她。
八抬大轿子后面是一众扈从抬着,扛着,披着红绸子的聘礼,乌泱泱的把街巷塞满了。阿娘私下里教过她,人间女子嫁娶,有八抬大轿,十里红妆。
“这个理由不错。不过,乌鸦怎堪配鸾凤。”朱彻面上笑了笑,他的笑是扯出来的,糅合了三分怜悯七分嫌恶。怜悯她只知钱财,嫌恶她不知廉耻。
刺啦啦的话钻进丫头秋豆的耳里。乌鸦吗?这男子确实是个乌鸦,只是皮相好看了些,秋豆暗想。丫头到底修为不够,参不透人话里的含沙射影。她眼里,小娘子是鸾凤也不够比的。俗世里的鸾凤也是俗物。
“可惜了,还是配上了。”齐瑟接话,模样温温柔柔,小意缱绻。
“我不想娶你。”
朱彻的一双眼睛犹如烟火凉透后的死寂——命由不得他,姻缘也由不得他。
“无妨,我只要人。”齐瑟稳了稳心神。复又抬眼看定了他:“又不要心。”
她想他心中的人儿大概是那个长福郡主。早该猜到了,听他亲口说出来,她的心没来由的发涩,大概红尘女子的心,疼起来便是这般,这滋味真不好受。阿娘跟她说过,世间最难参透的便是人的一颗心,它复杂辗转,情欲交织,真假相融,好坏参半......人自己都搞不懂,理不顺,还是不要的好!
朱彻看着这个小娘子贪婪又直白,恶毒又磊落,她墨墨黑的眼仁是清润明亮,勾着他往深里头沉,勾得他的心动了动;他记忆里也有这一双眼睛,坚韧,明亮,朝气。齐瑟的眼睛和他记忆里的那双眼睛重合了。
幼时的朱彻随母亲去武陵山边的别苑休养,他立在庭院里,看庭院里树木葱茏。忽地有清亮的声音传来:
“郎君可要吃五味子?”
一身白夏布衫子,头发乌顺齐眉的小娘子,伏在他别苑墙头,纱绢遮住了半张脸,手里拿一串红馥馥的五味子。正午的阳光照的那小娘子的眼睛,明润透亮,那是一个眼里有光的小娘子,不似他,他的眼睛里是一潭死水,无波无澜。他生来有疾,陷在这个富贵牢笼中,生不得,死不得。
世间相似之人何其多,怎会是她?不会是她。
也罢,娶谁都是娶,他一日一日浓酽酽的药喝下去,是知道自己活不长久的,母亲说齐家小娘子合了她的眼缘,那便娶了她。至少图来母亲的高兴。
仆人将红绸披挂的聘礼如流水一般,搬进了齐家主院。齐瑟的心欢快起来。她很快也能人间嫁娶,十里红妆。
3
夜色郁郁,芳龄稚齿的丫鬟们,挑了八对绛红纱灯,寂寂悒悒的引着朱红帷幔的喜轿进了长宁侯府。
齐瑟头上的销金盖头繁复华丽又厚重,她从五彩流苏下垂的缝隙中,看见自己十六幅的红罗裙,上头殷殷丝线绕成的缠枝牡丹,鸾凤和鸣。嫁衣的红色浓郁的铺天盖地,一重又一重。她的视线困在其中,困得满心欢喜。来拜堂的却是一只捆绑的大雁,仆妇们说是长宁侯染了风寒,拜不了堂。
后来,新过门的侯夫人齐瑟在仆妇小厮眼里是个摆设。长宁侯从成婚那日起就没进过她的院子里,而齐瑟成日待在院子里摆弄药材,每日辰时,申时送一碗汤药到老夫人房间。日日如此。
“细辛一钱,当归三钱......”齐瑟在院中拿着戥子称药。她在山野中修行千年,辨识百草。
“小娘子,秋豆替你委屈。那人日日喝的药是由你费了心思熬制的,如何要借老夫人之手?小娘子进门都三月了,他连院门都不曾进过。这岂不是痴心错付?”
“你都知道他连我院门都不曾进过,倘若知晓这药出自我手,他如何肯喝?”
日光透过百蝠菱纹格的窗户照进来,齐瑟黑墨墨的发,白净脸上双唇似抹胭脂未抹胭脂。她忽地垂了眼,面色凝重,低声说道:
“他喝药将补已有三月。秋豆,是时候了。”
“小娘子......”秋豆不忍:“小娘子,你舍得?”
狐族千年才修得一颗内丹,丹成之日,还需承受雷霆之劫,才可免去六道轮回,得享长生。秋豆是在问她,可舍得千年的造化?
“他病入膏肓,世间医药已是回天无力。倘若我舍了一生的造化,可得他活。我心下自是愿意。”
掌灯时候,长宁侯进了齐瑟的院子,红袍玉冠,俊朗韶秀。秋豆引着下人们都退了出去。
“母亲说,你有事寻我。”他声音寒凉,面如秋霜。
房中的熏香淡淡的散开,长宁侯忽忽若迷,不得动弹。
齐瑟靠近他,眉眼带笑。
“夫君,今晚洞房花烛可好。”她言语挑逗,有些咄咄逼人。
“.......你......”朱彻气急。
“我们成婚三月,并未有夫妻之实,所以今晚.......”齐瑟的话顿住。室内红烛昏昏,她恍恍惚惚,一瞬间以为自己跟俗世间女子一般,可以一夫一妻,恩爱不移,洞房花烛,生儿育女——她是狐,他是人!她是来报恩的,切莫乱了念想。齐瑟不由得心下一紧,指甲狠狠扎进手心,疼痛让她回了神。有些痴心妄想?简直痴心妄想。
在齐瑟五百多岁时,那个朝代,士族大夫都好炼丹修道,人人都想当长生神仙,不知怎么得知了狐狸千年修行的内丹能延年益寿,得享长生,便对狐起了杀戮之心,一个个都妄想夺丹续命;齐瑟的阿娘自幼便给她讲那条修炼成精的白蛇,恋上凡人,永镇雷锋塔的故事,告诫她俗世里的人最是懦弱无情,最是口是心非,人心最当不得真,也最是沾不得。
齐瑟回了神,细白的手指扯轻轻一扯衣带,将朱彻的大红锦袍脱落。朱彻只剩最后一层亵衣。他额上滲出密密的汗,简直羞辱难耐,一时间急火攻心,一口血吐了出来,人昏迷过去。
积年毒血终于吐了出来。
一粒莹白的内丹从齐瑟嘴中吐出,她急急又切切的喂他服下。积毒排出,内丹便可替他续命延年。齐瑟萎顿无力伏在朱彻身侧,她眼眸里影影绰绰,涣涣散散,似乎又见到那日,惊雷之下,山岳摆簸。她唬得魂魂魄魄不知当归何处,惶急误入一所宅院,塌上的人,一袭朱红广袖大袍,罩住她,细意安抚,护她周全......
恩虽已报,情却难了......
长宁侯府日渐热闹,朱彻骑马投壶,命色鲜活起来,齐瑟仰卧床榻,病了一场。老夫人派人延医问药,细意殷情,不时使丫鬟们端着各种金珠玉宝的赏赐,进得院子来来回回,热闹扰攘。
齐瑟收到朱彻那封信的时候,身子才将养好。信中五色纸,朱笔字。
“秋豆....”齐瑟问:“他这写的什么?”
人间的字,她怎会认得。
“小娘子,咱们出去找个识字的人,念一念不就可以了。”
侯府花园子里,春花开的正浓,齐瑟和丫头秋豆鲜少出来,一个穿青衣的小丫鬟捧着娇艳的花从穿廊走过。
“你可识字?”齐瑟拦住她。
小丫鬟见她不施脂粉,发间并无钗环珠冠。想是地位不高的。
“做侯府的丫鬟,自是识得字的!”
齐瑟将信纸递过去,笑意微浓的看着丫鬟。
小丫鬟自恃识文断字,未免卖弄,声音亮而扬。
“齐氏乃乡野之人,非我良配,与其两看生厌,不如一别两宽。信附休书一封。解怨释结,更莫相憎。”
闻声,有女子娇矜的嗤笑声隔着蔷薇花架传来。蔷薇花架上的花,团团簇簇,风华正浓。长福郡主娇若春花的伴着老夫人走过来。
青衣小丫鬟后知后觉,磕头求饶。
“长福,你先下去。”老夫人拍拍长福郡主的手。
花园子里的仆从丫鬟们拥着长福郡主噤声而退。
“阿彻去了江陵府。”
“哦。”齐瑟喃喃。
“因党派相争,他自幼中毒,即便我极力掩盖,他心下也知道自己是活不久的。如今得你救治,是阿彻的造化,也是我的造化。奈何他心中人并不是你,齐小娘子所图,我全可一一应允。但姻缘一事,由着阿彻自己的心可好?”老夫人言辞恳切。
要告诉朱彻,她是一只狐吗?告诉他,自己舍了千年的造化来救他吗?人怎么会喜欢狐呢?几百年前的那些追赶,杀戮,她一身冷汗。罢了....罢了.....没了内丹的她,寿数只剩十年,极易被修道术士发现。不如回自己武陵山看春花烂漫,四季轮回......
人间到底不是她待的地方。
4
阿娘自幼时便教她潜心修炼,积德行善,以便来日得道成仙,不受六道轮回之苦。阿爹阿娘终是没躲过雷霆劫,在齐瑟五百多岁时,形销骨散,灰飞烟灭。
光阴日日月月年年,齐瑟将将一千岁,祁洲已不叫祁洲,当下的人叫它江陵府,那一年武陵山下空置的别苑,住了人。那少年郎,朱衣墨发,冷眉冷眼冷面,日日困在雕梁画栋,富贵繁丽的楼阁里,好生可怜。
齐瑟一眼便看出他病入膏肓。她拿纱绢遮住半张脸,撷了一串五味子 ,伏在他别苑墙头 :
少年郎朱红长袍,苍白脸色,摇摇头。
“郎君有疾,多吃五味子!嘴里甜了,心头便也跟着甜。”齐瑟说。心中有善便是修行,五味子救不了他的命,给他荒芜的命运添些色彩,他能笑笑,也是好的。
“是吗?”他伸手接过那串红透的五味子,脸上笑笑,很是无望。
平地风起,齐瑟发丝浮动。
“谢你的五味子,这簪送你,束发。”
通透明润的玉簪托在少年郎手中,齐瑟接过,心头漾了漾。
齐瑟在山野林中,日日带了五味子来给他。她给,他便吃。忽地有一日,风云突变,阴云层层密布,疾风肃肃。齐瑟自知要应雷霆劫,必是九死一生。惊雷之下,她唬的魂魄不齐的当儿,惶急下化作狐,窜入别苑中,卧入塌上。惊雷直透过别苑卷棚劈过来,一旁琴光漆的楠木几案错折而塌。少年郎一掀衣袖,环住她,护她周全。
朱彻是人,雷无端劈不得。只落在朱红大袖上,焦黑一片,
“不怕,雷而已!”他说的缓而柔。
被他护在怀里的齐瑟,凝视朱彻一双浓如点墨的眼,不懂人世情爱的齐瑟便开了窍,动了心!
渡了雷霆劫,齐瑟回到洞府中只待丹成,后来再去山下的别苑里,却不见少年郎的踪影。
她凭着那支玉簪,在人海茫茫里寻寻觅觅多年,那日站在侯府厅堂里,看着那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老夫人。
“我要求嫁。”
“嫁谁?”
老夫人气急,指着脊梁骨骂她。齐瑟凑身过去说:
“长宁侯已病入膏肓,我可以救他。”
病入膏肓的朱彻,是老夫人的心头伤,她极力掩盖的真相被齐瑟揭开,痛难自抑。这么多年没有一个大夫能治好。齐瑟的话,又像干草上溅的一点火星子,老夫人本就熄了的心,又活了过来。
“怎么救?”老夫人急切。
“我擅医。可保他无恙。”
“你图什么?”良久,老夫人疑惑问道。
“图权势,图富贵,所以要嫁给他。”
原来心有所图,老夫人心下笑笑:这样的人目的明确,便信了她,能救朱彻,老夫人搭上命也愿意。
齐瑟就这么进了长宁侯府。
5
冬日的武陵山,树木萧瑟。
朱彻一身锦缎长袄,骑着白巅马,在落叶铺就的山路上缓行。
“我来武陵别苑有多久了?”朱彻瞧着重岩绝壑,山峦叠嶂的武陵山。
“侯爷,您来别苑都待了有大半载了。”老仆清了清嗓子,拿眼瞅瞅朱彻:“每日除了在山里头转悠,便是回别苑里枯坐。”
说完话的老仆摒气凝声,这一年来老夫人的信件跟雪片似的送过来,急着要小侯爷回京。
“侯爷可是有事未了?再晚些这冬日山里一落雪,寒凉的很。不如早些回京。”老仆又道。
“再等等。”他声音落寞无奈,目光陷在山头氤氲的雾气里出不来。
等什么呢?老仆想问,话冲到嗓子眼里,却又知趣的闭紧了嘴。
山路上有皂衣芒鞋的道士迎面而来,面目肃杀,他立于道左,双眼直盯着朱彻,神色疑惑。良久说到:“怪哉!怪哉!檀越身无俗世之气,可是修道之人?”
“我家主子,自是贵气天成。你少见多怪了。”老仆截了道士的话,一手揽牵马,向山脚下走去。
“荒山野岭,恐有妖孽作祟,檀越可是得小心呐。”道士声音却低沉得只有他自己能听到。
白颠马踏在厚厚的落叶上有细碎断裂的声音。皂衣道士一双眼阴恻恻望向背身远去的朱彻,面带狞笑,山底处粉墙黛瓦,楼阁宏丽的别苑让他分外眼明。
夜间,武陵山忽地细细密密的下起了雪,待到天明时,别苑的门前青石台阶上已是全白了。齐瑟穿就一双织锦云纹鞋,浅浅的陷在台阶上的白雪里,烟色折枝梅花的斗篷下露出一段绯色罗裙。
朱漆铜环的大门在呜咽的风雪中紧闭。齐瑟立在青石台阶上,半抬了手想去叩门,门环上的森森凉意,让她心内一怯。秋豆告诉她,武陵山已非藏身之处,有道士寻踪,如若不逃,她们阖族必无善果。此去北徙太白山,南北相隔有千里之遥.......没了内丹的她是一介凡身,如何才得相见?
她此番就再瞧瞧他。
忽地别苑朱漆铜环的大门被仆人从内里打开,水磨青砖的地面上白雪皑皑,八十四骨的油纸伞下,朱彻锦缎直裰,外罩了丝绒鹤氅,立在庭院中。
有飞雪落在伞上簌簌作响。朱彻看着门首处的小娘子,烟色斗篷兜帽下,一张脸澄净温婉,模样端好如画中人。
他魔怔了,踩着一地乱琼碎玉走向她,眼前的小娘子眉眼皆如故人,他心中百转千回,念念不忘的那个故人。
“郎君许久不见,可还好。”齐瑟寒暄。
呵,原是齐家小娘子,朱彻清醒过来,看向她的模样已是冷眉冷眼冷面。
“妖孽哪里逃。”院外有道士凌厉狠绝的声音惊若雷霆。
闻声齐瑟双眼凄凉,身后道士眼里磨刀霍霍,手中拔剑相向。青铜所制的剑身,挑着黄色朱纹的符箓,直直从背后刺穿她的心窝,她往前趄列几步,扶住朱彻。温热的血溅了他一身,血珠渗入他白绫直裰里,猩红点点。
她一抬头,眼神便软了下来,面如冠玉,眉眼如画的朱彻,一如当年初见时。她把他放在心里百转千回,喜乐悲苦独享!
森冷的凉意从齐瑟心窝漫至全身,她很有些耐不住这刺骨寒凉。
“郎君,可要吃五味子?”齐瑟扶靠在朱彻肩头,声音哑暗,虚弱尘灰的问他。
故人当年也是一句“郎君可要吃五味子?”朱彻的心似破了一道口子,里头寒风凌厉。不由得手也忽的密密瑟瑟的抖,他拼了命的压制,却压不住。
“你在......说什么?”朱彻悲恸,恐惧深入他的四肢百骸。
他双手环住她,烟色兜帽脱落,齐瑟乌黑的发髻上那根玉簪,莹润明亮。
这不是当年他所赠故人的么?故人今何在?
“你缘何杀她?”朱彻朝道士怒目相向,杀气腾腾。
齐瑟烟色斗篷下,银白的狐尾露出。逐渐幻化为狐,伏地而死。
“妖孽而已,檀越身有仙气,必是得了此狐内丹,才能续命延年。何不再与贫道联手,绞杀其族。”道士愈发疯魔,“如此,我等皆能得做长生神仙。”
朱彻悲愤的双眼通红,运气合力将手中八十四骨紫竹柄,直破道士眉心......
雪在寒风中如扯絮飞花,漫天漫地。
武陵山中,有哭声缈缈,初闻时悲凉,再闻凄惶难抑。
6
十六年后。
坊间流传长宁侯有断袖之癖,龙阳之好。长宁侯至今未曾娶妻纳妾。奈何年近四十的长宁侯,还是一副清秀俊逸,少郎君的模样,这十几年来,惹的官媒的那些婆子们,年年往府上跑。
长宁侯府向来回绝是不娶不纳。
这几日长宁侯府的老夫人收到了朱彻从江陵府送来的信,已是满头银发的长宁侯府的老夫人,喜笑颜开给一家家世族们亲自派喜帖,说是长宁侯要娶亲了,京里头世家贵族们炸开了锅。
有和老夫人交好的贵妇会多问一句:“哪家小娘子,这么有福气能嫁的阿彻这般谪仙般的人儿?”
老夫人脸上讪讪的笑答:“还不知是哪家娘子。”
这么多年了,看着媒婆一个个势在必得进得府来,最后都垂头丧气的离开长宁侯府,老夫人百抓挠心啊!前几日,甫一收到朱彻信中说要娶亲,连忙一壁发派喜帖准备聘礼。一壁“羽缴文书”的速度唤江陵府别苑的老仆火速回京。
“那小娘子芳龄几何?”老夫人问
“才将将十五。”
“哪家的小娘子?”
“还不知道。”老仆擦擦汗。
“如何相识的?”老夫人又问。
据老仆回忆说那日是这样的。
“砰...砰....砰”
武陵别苑的朱漆大门响起了敲门声。
门被老仆打开,一位牵着青骢马的小娘子停门首,绯色襦裙,白纱维帽。
“阿伯,山路行乏了,讨些茶水喝。”小娘子声音软糯清亮。
“小娘子请入内。”老仆说到。
小娘子的云缎绣鞋踩在水磨青砖上有些雀跃。
“老伯,好生奇怪,这院子我似乎来过。”
一转身,松荫蔽日下,眉眼如画的朱彻,一身白绫长衫跪坐竹簟上,面前的几案上,青色瓷盏中翠色茶水。
“是吗?”朱彻反问。
他推过来一杯茶水。小娘子接来一饮而尽。
“好茶。”
她忽的一手掀开轻薄的帷纱,朝朱彻摊开细白的手,一簇红馥馥的五味子团在掌心。
“郎君,可要吃五味子?”帷纱里的小娘子一张脸,风华绝代,满是笑意告诉他:“谢你的茶水。”
朱彻呆怔住,直看着面前的小娘子,眉眼如故,笑靥如故.......
“你可是故人复再来?”朱彻双目潸然。
长宁侯大婚那一日,嫁妆是从江陵府走水路到的京城,红恍恍的嫁妆从京城外的护城河里连绵不断的送到长宁侯府。
“怕是皇帝嫁女儿也没这般排场。”看热闹的老妇人道。
“都说十里红妆难见,今日这算几里红妆啊?”有女子艳羡。
长宁侯府上的三两个青衣丫鬟仆妇聚花园子里的廊下,在一起咬耳朵:
“听说新夫人所有的嫁妆全是侯爷给置办的?”
“可不是,侯爷说了新夫人最爱钱财,所以可劲的满足她。”
“老夫人可是把压箱底的宝贝疙瘩都拿出给新夫人当嫁妆了。”
当日在洞房中伺候的上了年纪的妈妈又爆了个秘辛说;“你们年纪小不知道,这新夫人和侯爷以前休掉先夫人可是一模一样......”
花园子里有长宁侯温和的声音传来。
“夫人,这蔷薇花架可好?”朱彻在花园子里一头撑了青绢凉伞,一头替新夫人摇扇。
“不好。”新夫人摇摇头。
“来人,把这蔷薇花架撤下去......”朱彻唤到。
“夫人,午膳可用的满意?”
“夫人,明日叫长兴班来唱梁祝如何?
“夫人,冬日武陵山赏雪最好,咱们一块去。”
“夫人......”
廊下仆妇都笑笑,四下散了。作品名:《齐瑟》;作者:竹淼